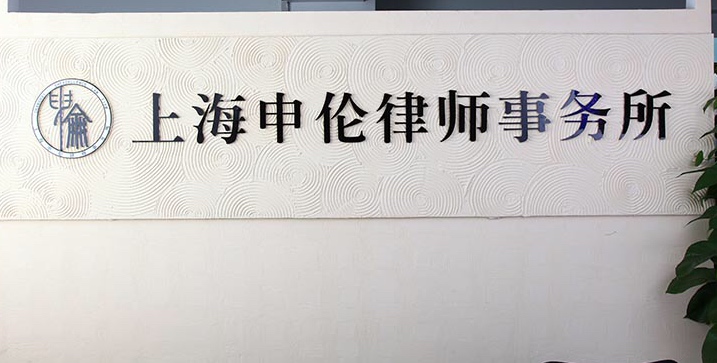
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
1.王保亮、梁子浩股权转让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65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王保亮认为,原判认定其存有抽逃资金依据不充分。经查,本案经二次审计鉴定,原判认定事实依据的鉴定结论,系由具有法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亦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王保亮虽提出鉴定机构鉴定时的资料不齐全,但未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绍天和专审字[2015]第002号司法鉴定审计报告显示,盛德公司第一次增资的500万元存在变现抽回或抽回资金情形,王保亮抽回420万元,梁锡林抽回80万元;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的1000万元,王保亮抽回448.7911万元,梁锡林抽回467.1091万元。现王保亮不能提供证据推翻上述鉴定结论,原判认定王保亮存有抽逃出资有相应依据。
2.张章生诉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再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58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本院认为:在实缴资本制下,股东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为:(1)主体为股东。(2)主观方面为故意。(3)客体。股东抽逃出资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司的合法权益和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4)客观方面,抽逃不同于一般的交易,一般的交易是有公正、合理的对价,但“抽逃”是指股东出资资金或者相应的资产从公司转移给股东时,股东并未向公司支付了公正、合理的对价,即未向公司交付等值的资产或权益。这也是认定抽逃出资行为的关键所在。乐清伟业公司与宁波中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挂账的预付款在账面上也在乐清伟业公司与宁波中缝公司的实际交易中逐渐减少。且乐清伟业公司的股东(张章生51%、周芝瑛49%)也均予以认可的情况下,张章生向宁波中缝公司借款的行为结合乐清伟业公司向宁波中缝公司供货,并未使公司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不符合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权益受损的客观要件。
3.嘉兴市××有限公司等诉嘉兴市××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浙民二终字第155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至于新××公司提出500万元和98万元均系股本金,不得收回的问题,由于在签订协议之时,新嘉××办事处与新××公司、新都××与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已无投资关系,已非两公某股东,故并不存在抽逃股本金的问题,且对于新都××而言,500万元系支付给新嘉商业公某的借款,即便新嘉商业公某此后将该款作为股本金投入新××公司,亦与新都××无关,98万元虽系新都××直接支付给新嘉基础设施公某,但协议书中的偿还主体为新××公司,并非新嘉基础公某,因此,同样不存在抽逃注册资本之说。
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主张上海世茂公司通过案外人牡丹江茂源抽逃出资,在牡丹江茂源并非本案当事人的情形下其提供的相关证据的证明力无法确认。且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仅提供了杭州世茂公司2010年度的审计报告、牡丹江茂源2011、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和上海世茂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以及部分的资金流水明细,并不能完全印证牡丹江茂源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应收款及杭州世茂公司对牡丹江茂源的应收款以及杭州世茂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债权之间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因此,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海世茂公司抽逃出资,故对其提出的上海世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5.某公司与邱某某等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难以认定讼争的290.5万元是南亚公司抽逃的出资。1.从该290.5万元款项的来源和组成看系经某公司调账而成,并非某公司直接支付南亚公司。从法律角度,该调账应属债务转移,是南亚保龄球公司和总户中的其他单位将各相关债务合计290.5万元转移给南亚公司承担,但某公司没有提供原始凭证证明该调账经相关当事人协商一致。2.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仅凭某公司提供的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向杭汽轮公司出具的浙东会专[2007]1061号资产审核报告,不足以认定南亚公司抽逃290.5万元出资。某公司提出抽逃出资一般记载为“其他应收款”并无依据。此外,某公司提供的浙东会专[2007]1061号资产审核报告具有一定局限性,一是该报告系受某公司的股东杭汽轮公司的单方委托而出具,并非受某公司或全体股东委托;二是该审核报告在“保留及其他事项说明”中认为讼争290.5万元经核实是南亚公司在某公司成立后投资款抽回挂账。但对“经核实”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确凿充分,未作进一步列明;三是该报告对使用范围作出限定,该审核报告在“其他主要事项说明”中载明,报告仅供杭汽轮公司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四是该资产审核报告并非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报告。3.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南亚公司的相关审计报告没有载明某公司有290.5万元款项汇入。综上,某公司认为南亚公司抽逃290.5万元出资的诉讼主张,依据不足,也与其提供的2002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反映的内容不符。
6.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等与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601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从温州分公司举证看,其证据主要是其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两份报告书。一份是浙江正大资产评估公司2003年6月23日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载明“国际广告公司投资给温州分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其中1845650元已抽回,至今未到位。”另一份是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2004年4月7日出具的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载明“当年国际广告公司就抽回资本金1845650元,挂账于其他应收款中。”该两份报告书虽未附相关财务凭证,但对于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资本金的结论意见是一致的,温州分公司对其诉讼主张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国际广告公司上诉认为其提交的温州分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和历年年检报告书两份反驳证据可以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经查,该两份证据载明温州分公司的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为200万元,但该记载并不能证明国际广告公司未有抽回资本金的行为。温州分公司历年年检报告书虽然记载的应收款余额均小于1845650元,但应收款余额系应收款与应付款相抵后的记载数额,抵扣后有可能发生应收款余额小于抽回资本金数额的情形,故应收款余额的记载也不能直接推翻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载明抽回资本金挂账于其他应收款的情形。国际广告公司的该两份证据并不足以反驳温州分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故温州分公司主张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7.王文年等诉温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等抽逃出资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原审法院认定王文年抽逃出资,有相应依据。理由是:1.王成标于2016年1月18日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证实王文年仅出资10万元,标峰公司注册资本中的800万元系融资垫资,在公司设立后已归还。2.王文年2016日1月19日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承认其出资为10万元,虽然原审庭审中主张其出资120万元,但至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3.标峰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可证明标峰公司验资的800万元来源于胡珺的存单等,后该款在同一时间内作为标峰公司股东的出资。在完成验资后,上述款项先转入王成标账户,再通过危平账户转为胡珺的存款。标峰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证明标峰公司的注册资本被抽逃的事实。
8.张颖斐等诉张松伟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再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本院认为,首先,张松伟、张绍平对其主张的柏莱公司与郑洁、柏莱公司与阿尔凡公司、柏莱公司与外方客户分别存在的货物买卖关系,并未提供交易合同文本、货物交付凭证、结算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其次,柏莱公司对收到的上述400万元款项,在其原始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款项性质为“周转款”,而非货款;再次,正常情况下,作为买方的外方客户向作为卖方的柏莱公司付款,一般会直接汇入柏莱公司账户,而不会汇给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其他人,在张松伟、张绍平、阿尔凡公司、郑洁未提供证据证明柏莱公司委托其作为受托人代收货款及柏莱公司指示外方客户将款项支付给其受托人的情况下,张松伟、张绍平的上述抗辩,不能成立。据此,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以购货等名义分别将柏莱公司2995900元、150万元、1899481.80元转至关系人或配偶或关系人投资设立的公司名下,且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系正常交易,二审结合柏莱公司管理人在接管公司财务账册后没有发现任何相关交易的合同、发票、入库单、账面存货记录等事实,认定上述三人的行为系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构成抽逃出资,有相应依据。
9.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月新、陈继泉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终2538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本院认为,其一,相关司法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报告并未考虑上诉人系改制企业性质,且未就可能存在的上诉人及股东代偿原企业债务、弥补原企业亏损及投入列入审计范畴,同时上诉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属于司法判断权,鉴定机构无权进行评判。其二,因上诉人系原集体企业上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政策性改制形成,周月新等七人以零资产受让原企业,并对价支付了原企业相应无形资产,当地政府根据上级要求主导推动并办理了工商执照、资质证书变更、注册资金连续等改制工作,现两者工商登记仍属一户,且原企业注册资本金经工商登记为3331万元。同时,在改制前后,两企业存在人员、资质、未竣工项目管理等延续性。通过上述方式将原集体企业整体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虽上诉人形式上是按设立登记要求提交文件,但并非纯粹的新设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企业公司制改造性质,具有政策性特点。本案部分出资款去向并不确定,即使本案部分股东存在将其他部分出资款转入公司帐户验资后又转出行为,但该行为是否损害公司权益并不确定。据此,本案不能认定为系抽逃出资行为。
关于名义股东抽逃出资的认定
1.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等与浙江××学院不当得利纠纷申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民提字第11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中××信托作为求是××的股东其应当按照公某法和公某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但本案中,中××信托除按委托人通用××的要求将1200万元资本金打入求是××及向公某委派董事、经理外,并没有实际履行任何管理、经营之责。根据本案查某的情况,求是××于2002年12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金为1500万元,其中中××信托认缴1200万元;但就在公某成立的次日,即2002年12月4日,中××信托委派的公某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也是通用××的法定代表人高×又将上述注册资本金全部抽逃转回通用××,其行为明显违反公某法和公某章程的有关规定。中××信托作为公某控股股东,本应依法维持公某资本金稳定,以确保债权人利益。但中××信托没有依法履行相应股东职责,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否则,委托人可能利用信托制度存在的不健全之处规避法律责任,造成权责失衡或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不良现象。--中××信托的股东责任也绝非提供一个资金往来账户,将信托资金打入公某账户这么简单,而是应该按照公某法、公某章程完整履行公某股东义务。中××信托从未过问公某的资金调度,从未参加公某的董事会,履行董事职责。其放弃公某股东职责的行为对公某资本金在成立次日即被抽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公某法股东须维持资本金稳定的规定,原审认定中××信托在其认缴注册资本金的范围内对通用××抽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2.吴晓颖与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等追索代付款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商终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吴晓颖对丈夫吕盛荫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1)永康市良宝动力工具有限公司被增资后提高了公司向银行贷款额度,表面上是公司受益,实质上是股东受益,吴晓颖作为股东也不列外。此外,吕盛荫增资后又抽逃出资是为公司所为,并非用于个人事务。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上加盖的吴晓颖私章系其留在公司财务保管的章。吴晓颖称此期间其在国外读书,但并非属下落不明,况且吴晓颖和吕盛荫也非夫妻关系不好,吴晓颖和父母之间也不存在关系不好,故在现代通信发达的时代,他人有理由相信吕盛荫的所为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2)吴晓颖未举证在2000年8月(即其与丈夫吕盛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良宝工具公司变更成立时,吴晓颖名下的股份系其个人婚前财产。2004年,吕盛荫作为丈夫对吴晓颖名下的股份进行增资及抽逃出资等,系属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共同共有财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夫妻双方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3)本案兰歌公司追偿的系其已为良宝工具公司清偿的债务,作为良宝工具公司的股东本身就应对公司负责。据上,吴晓颖和丈夫两人对抽逃出资部分应承担连带责任。现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选择夫妻一方吴晓颖对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令吴晓颖在抽逃出资部分范围内承担责任正确。
3.吴艳艳等诉永嘉艳阳纸箱有限公司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607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吴艳艳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明白在章程和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其在签名成为艳阳公司的股东后,不得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或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吴艳艳在缴纳出资90万元后,将总计702710元以借款、往来款名义从艳阳公司账户转入其个人账户。虽吴艳艳抗辩该个人账户非为其掌控,款项也非为其收取,但吴艳艳对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该账户由吴艳艳开设,除被盗用等非为吴艳艳行为造成的情况外,吴艳艳应承担该账户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即使吴艳艳存在出借个人账户的情况,亦不能免除吴艳艳归还702710元出资的义务。此外,吴艳艳作为工商登记持有艳阳公司60%股份的股东,在艳阳公司未能偿还债权人欠款经破产程序后由艳阳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吴艳艳追收抽逃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管其在本案中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吴艳艳抗辩其为名义股东无需承担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协助抽逃出资的责任承担
1.桐乡市崇福宏王达裘皮制品厂等与嘉善诚洲企业登记代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侵害债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浙商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由于没有资金,顾忠华通过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让诚洲公司垫资5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在金巴蕾公司成立后,诚洲公司根据事前与顾忠华协商好的意见,以支票形式从金巴蕾公司的基本帐户上抽逃注册资本50万元,以归还金巴蕾公司注册时诚洲公司帮助投入供验资用的借款。诚洲公司作为一个从事代理企业登记的单位,应明知注册资本的性质和用途,在股东没有投入的情况下提供资金成立金巴蕾公司,则该投入的资金即属于金巴蕾公司的财产。但是,诚洲公司却在金巴蕾公司成立后即与顾忠华等人一起抽逃已经属于金巴蕾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用以偿还成立金巴蕾公司时用以出资的借款,使金巴蕾公司从成立一开始就因股东出资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责任财产,让金巴蕾公司股东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却披上“合法出资的外衣”,致与金巴蕾公司进行交易的主体处于危险境地。诚洲公司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包括宏王达厂在内的金巴蕾公司债权人的财产权益,诚洲公司在整个过程中行为主动,态度积极,诚洲公司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且诚洲公司的侵权行为与宏王达厂所受债权损失有因果关系。诚洲公司的行为等同于甚至严重于给金巴蕾公司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验资机构出具不实或虚假验资报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和通知,诚洲公司应当在金巴蕾公司股东无法补足出资的金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浙XX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杜利法、李永儿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初400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本院认为,本案系管理人以公司股东及高管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为由提起的破产衍生诉讼,应为追收未缴出资、抽逃出资纠纷案件。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杜利法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情形;二、如果杜利法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情形,李永儿、何兴祥、李萍儿作为董事,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华夏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关于华夏公司破产受理日报表的审计报告一份,虽然该审计报告并非第三方制作,且李永儿、何兴祥对审计报告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杜利法本人并未提出异议,且该审计报告系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形成,李永儿、何兴祥虽提出异议,但也明确表示不申请审计,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予确认,可以认定杜利法通过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虚假出资350万元,验资之后,杜利法又通过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抽逃注册资本100万元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董事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的前提是其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协助抽逃出资,本案中,李永儿虽然是华夏公司副董事长,但其并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未在公司领取报酬,何兴祥在杜利法出资时并非公司董事,华夏公司要求李永儿、何兴祥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李萍儿系公司董事、杜利法妻子,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华夏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股东涉嫌抽资、虚假出资在公司账面反映为其他应收款中,华夏公司对李萍儿应收款为1570万元,李萍儿的行为构成协助抽逃出资,华夏公司要求李萍儿对杜利法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等诉孙成杰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丽商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摘要】
本院认为,被告孙成杰作为实际控制人、被告李静作为股东在设立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的过程中利用虚假购销合同抽逃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的事实,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松阳县人民法院(2012)丽松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书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20日发布)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作为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诉请被告孙成杰、李静在抽逃出资数额范围内对其未受清偿部分的债务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朱建国、蔡俊杰及崔婷分别为案涉5000万元款项的出借人或款项往来具体经办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条“删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以及第十三条“本决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股东出资相关纠纷案件,适用本决定;本决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决定。”的规定,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请前述三被告承担因被告孙成杰、李静抽逃注册资金而产生的相应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附:案例原文
王保亮、梁子浩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浙民再6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保亮。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晟杰,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婷,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子浩。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浩杰,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水根,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保亮因与被申请人梁子浩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终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浙民申115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王保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晟杰,被申请人梁子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浩杰、王水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保亮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二审法院据以定案证据的司法鉴定审计报告认定,王保亮、梁锡林均有抽逃增资的行为,但梁子浩系梁锡林之子,如王保亮确有抽逃增资,梁子浩在受让股权时也是明知的。1.审计报告(绍天和专审2015第002号)认为,宁波盛德汽车零部件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公司)2008年10月第一次增资的500万元存在变现抽回或抽回出资的情形,其中王保亮抽回420万元,梁锡林抽回80万元;第二次增资的1000万元,存在变相抽回出资(增资)资金共计915.9002万元,其中王保亮占448.7911万元,梁锡林占467.1091万元。如王保亮确有抽回增资的行为,梁子浩在其受让盛德公司49%股权时亦是明知,因为梁子浩系盛德公司大股东梁锡林的儿子,梁子浩在受让时必须经过梁锡林同意。2.王保亮将其持有的盛德公司49%股权转让给梁子浩,系梁锡林的要求,其实质是王保亮退出公司,将公司交由大股东梁锡林控制,而梁子浩系梁锡林的儿子,故梁子浩并非单纯的第三人受让股权,梁子浩完全清楚当时盛德公司的财务、出资情况。《股东协议》中写明“由于盛德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均由王保亮负责,另一规定梁锡林实际不参与管理,导致股东之间不和谐因素,为促进盛德公司和谐发展,王保亮有意转让其在盛德公司的全部股份,梁子浩同意受让”。可见本次股权转让是盛德公司两股东(王保亮、梁锡林)协商由谁退出公司、谁全部掌控公司的结果。由于梁子浩与梁锡林系父子关系,两人一起经商多年,所以王保亮才应梁锡林要求将股份转让到梁子浩名下。3.从生效的民事判决可知,梁子浩在受让盛德公司股权前,就清楚知道盛德公司资产、出资情况。在本案一审前,梁子浩曾另案起诉王保亮,当时梁子浩以盛德公司存在资金黑洞,公司资产严重不实,王保亮有抽逃出资行为,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股东协议》,该案由生效判决驳回了梁子浩的诉讼请求。而该一、二审民事判决均认定“签订《股东协议》前夕,梁子浩带专业律师汪家生在童国英陪同下,对盛德公司及控股的四个子公司进行考察”、“梁锡林与梁子浩是父子关系,而梁锡林是盛德公司的大股东,应当清楚盛德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梁子浩完全可以从梁锡林处了解盛德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财务情况”、“股权转让时,王保亮不可能存在对梁子浩有隐瞒或欺诈行为”。但梁子浩事后反悔,不愿继续付款,先是以受欺诈为由要求解除《股东协议》,败诉后又通过向已被其控制的盛德公司补缴增资款的方式,来主张双方债务抵销,进而逃避付款义务。二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明,反而支持梁子浩不诚信的行为,显属错误判决。二、签署《股东协议》时盛德公司资产约有1800万元,双方均清楚盛德公司的实际价值,且转让股权时双方有竞价过程,故1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是净价,并不包括补缴公司增资部分。签署《股东协议》时,王保亮与梁子浩对盛德公司的价值都十分清楚,所以双方没有再对盛德公司资产进行审计。依据盛德公司及子公司2009年在工商备案的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可知,当时盛德公司及子公司资产有1800多万元,且几家公司对外均无负债,也无银行贷款。几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很好。所以当时王保亮、梁锡林均有受让另一方股份的意思表示,且双方有竞价的过程。具体是梁子浩代表梁锡林与王保亮谈判、竞价。在生效的(2012)浙绍商终字第204号民事判决就认定“双方协商之初,在王保亮也曾提出过以960万元受让梁锡林51%的股权以控制整个公司,双方均有受让另一部分股权的意向,存在一个询价、磋商的过程”,可见,当时的1200万元的转让价是王保亮所拿的净价,并不包括补缴公司增资款部分。三、事实上王保亮并无增资后抽逃的行为,王保亮在一审中已提供证据予以证明。1.审计报告认定第一次增资后王保亮抽逃420万元的情况不存在。该款项实际是2007年7月盛德公司受让王保亮持有的宁波奥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德公司)70%股份后,应当支付给王保亮股权转让款500万元中的一部分,该款项最终流向梁锡林、童国英(系梁锡林聘请的公司财务总监)的账户,若有抽资也是梁锡林抽资。2.审计报告认定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1000万元后,有796万元流入盛德公司的子公司,即奥德公司310万元、宁波海曙宝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公司)186万元、宁波奥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星公司)310万元、宁波市鄞州区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驰公司)100万元,进而认定王保亮增资后抽逃,但该事实也不存在。3.审计报告认定盛德公司从兴业银行宁波海曙支行账户电汇170.9002万元至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企业账户的这笔款项,认定与凭证在支付对象、支付时间或是支付金额均不一致。审计单位错误将二个毫不相干的事情混为一谈。四、退一步讲,即便如二审法院所说王保亮有增资后抽逃行为,那梁子浩也是明知股权有瑕疵仍表示接受。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王保亮就股权瑕疵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即使之后,梁子浩代为补缴盛德公司增资款,亦不能就此再向王保亮主张权利。五、盛德公司与梁子浩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时,已完全被梁锡林、梁子浩父子掌控。梁子浩代为补缴公司增资款的真实目的是想逃避付款义务。;梁子浩与盛德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后,梁子浩就立即通知王保亮要求债务抵销,并拒绝再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但直到半年后,梁子浩才支付盛德公司1040万元对价,而该款项是何性质,是否也存在被抽回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梁子浩代为补缴增资款是假,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梁子浩通过已被掌控的盛德公司,以债权转让、债务抵销方式,来达到不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的目的。对此,二审法院并未查明,仅从公司资本维持的角度,机械地看待本案,其实质是纵容梁子浩的违约。王保亮庭审中又补充的再审申请理由:案涉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王保亮有抽逃出资行为的证据,鉴定的检材程序不合法,检材的来源一部分是法院案卷,一部分是盛德公司直接提供给鉴定人员,均未经过质证和原审法院审核,而盛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梁子浩。本案案由股权转让纠纷,原审法院以此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定案,但如果梁子浩主张债务抵销,应在前一个案子执行程序中主张,本案诉讼不是新的诉讼。股东的抽逃出资即使存在,本案的原告应是公司,被告是梁子浩,公司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追偿不是可以转让的合同权利,而是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财产侵犯的侵权之债,梁子浩受让债权后行使这个权利是不成立的。侵权之债应由公司提出主张,由法院确定后,公司再转让给梁子浩,梁子浩才可行使抵销权。综上,王保亮再审请求:撤销(2015)浙绍商终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梁子浩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梁子浩再审辩称:坚持一二审的诉辩意见。另补充:一、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正确,梁子浩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受让盛德公司对王保亮的债权后,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与王保亮付款义务依法抵销,系《股东协议》权利义务终止的一种法定情形。梁子浩的诉请属于股权转让纠纷。二、王保亮抽逃出资事实依据充分,证据确凿。王保亮在盛德公司两次增资过程中抽回或变相抽回869.2811万元,该事实已经上虞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查实。三、王保亮、梁锡林抽逃出资,不能推断梁子浩知道或应当知道抽逃的事实。四、股权转让对价1200万元包括王保亮应当补缴的增资部分。五、梁子浩可以受让盛德公司对王保亮的请求权,并进行抵销。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王保亮抽逃出资依法应当对盛德公司承担出资返还义务,盛德公司对王保亮享有的债权为法定债权,债权内容为出资返还。盛德公司依法可以转让上述债权,该债权不具有专属性。六、盛德公司依法将债权转让与梁子浩,该等转让已经生效、梁子浩对王保亮债权债务依法可以抵销。梁子浩于2012年6月15日依法将通知书送达王保亮,明确梁子浩依法将债权抵销梁子浩与王保亮签订的股东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并要求王保亮支付超过王保亮债权范围部分的债务。七、盛德公司的减资、注销与本案无关,系盛德公司独立的经营行为。梁子浩支付了盛德公司债权转让对价,至于盛德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如何使用以及盛德公司减资、注销均与本案无关。盛德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及需要进行独立经营。要求驳回王保亮的再审请求。
2012年6月14日,梁子浩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要求确认梁子浩《股东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998.73万元款项已经与王保亮对梁子浩的债务抵销;2.判令王保亮协助梁子浩办理全部剩余39%受让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保亮承担。
上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盛德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8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王保亮出资245万元,占股权比例49%,案外人梁锡林出资255万元,占股权比例51%。该公司投资设立了奥德公司、宝盛公司、奥星公司、东驰公司四个子公司。2008年10月,盛德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同意以货币增资5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其中王保亮增加出资245万元,梁锡林增加出资255万元。王保亮245万元投资款于2008年10月16日到账,梁锡林255万元投资款于2008年10月15日到账。2008年10月17日,宁波文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新增出资进行审验,出具文会验字[2008]1144号验资报告,同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08年10月27日,盛德公司以“长期投资”的名义从盛德公司划出350万元至奥德公司,奥德公司账面反映为“长期应付款”。2008年10月28日,奥德公司以支付材料款名义开出现金支票80万元,支票存根写收款人“奥德(扬兴)”,而实际在银行留存的该支票正联反映是以“差旅费”提取现金,同日徐碧波(奥德出纳)存入梁锡林账户80万元。2008年10月30日,奥德公司以材料款名义开出转账支票270万元,支票存根写收款人“鄞州扬兴”,而实际在银行留存的该支票正联反映是“归还借款”名义转入王保亮个人账户270万元,并且未发现奥德公司与王保亮之间存在借款关系。2008年10月28日,盛德公司又以“长期投资”的名义从盛德公司划出150万元至王保亮个人账户,财务将该款项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属于虚假账务处理。盛德公司第一次增资的500万元投资款,在资金到位后,其中的150万元直接划入股东王保亮账户,另通过下属奥德公司划入王保亮账户270万元,合计420万元,该两项划款账面反映内容与事实不符,属于虚假账务处理,王保亮存在抽回或变相抽回出资(增资)资金420万元的情况。2009年2月,盛德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进行第二次增资,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增资1000万元,其中王保亮增加出资490万元,梁锡林增加出资510万元。王保亮490万元投资款于2009年2月16日到账,梁锡林510万元投资款于2009年2月17日到账。2009年2月17日,宁波文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新增出资进行审验,出具文会验字[2009]1008号验资报告,同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的1000万元投资款的资金来源实际是王保亮和梁锡林向案外人童强项个人借款。其中,王保亮借款490万元,梁锡林借款510万元。增资手续办完后,盛德公司划出资金796万元至下属四家公司,其中划入奥德公司310万元(2009年3月9日划入180万元、2009年3月11日划入130万元),划入奥星公司200万元(2009年2月26日划入),划入宝盛公司186万元(2009年2月26日划入140万元、2009年3月9日划入46万元),划入东驰公司100万元(2009年3月5日分两笔各划入50万元)。盛德公司划入奥德公司的310万元,奥德公司财务账面反映为“长期应付款”。奥德公司于2009年3月2日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开出六张转账支票共计310万元,银行留存的支票正联反映上述转账支票均是以“借款”名义划入葛迈丽(奥德会计)个人账户,奥德账务处理反映为“其他应付款-宝马部”。葛迈丽于2009年3月10日和同年3月11日分别存入童强项个人账户180万元和130万元。经查证奥德公司与葛迈丽之间没有经营业务往来和借款关系,划款理由不成立。盛德公司与奥德公司对于划账310万元双方账务处理不对应,支票存根联与正联反映内容不相符。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1000万元投资款中的310万元出资(增资)资金通过奥德公司,利用虚假账务处理的手法,掩盖资金真实流向,实际上已存在变相抽回的情况。盛德公司划入奥星公司的200万元,奥星公司账面反映为“长期借款”。奥星公司于2009年2月26日以“差旅费”的名义提取现金40万元,同日,奥星公司原财务人员林盼盼将40万元存入童强项的个人账户。2009年2月27日,奥星公司开出转账支票划出160万元至王挨亮的个人账户,奥星公司账面做“其他应付款-王挨亮(装修费)”处理。经了解奥星公司与王挨亮无装修业务关系,转给王挨亮的160万元实际已转入童强项的个人账户。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1000万元投资款中的200万元出资(增资)资金通过奥星公司,利用虚假账务处理的方法,掩盖资金真实流向,实际上已存在被变相抽回的情况。盛德公司划入宝盛公司的186万元,宝盛公司财务账反映为“其他应付款”。后以差旅费、备用金等名义提取现金90.5万元,开出转账支票95.5万元,合计186万元。其中2009年2月26日至2月27日提取现金64.8万元(2009年2月27日19.8万元是转账支票,划入童国英个人账户),宝盛公司2009年2月28日50号凭证反映归还童国英借款56.5万元,但宝盛公司账上与童国英之间没有借款事实的依据。另银行提供的单据显示公司财务人员赵杰燕于2009年2月26日、同年2月27日分别存入王保亮个人账户30万元、15万元,2009年2月27日由赵杰燕将王保亮个人账户中的45万元转入童强项的个人账户。2009年3月3日至3月5日提取现金25.7万元,宝盛公司2009年3月31日79号凭证反映归还王瑞斌借款25万元。银行提供的单据显示赵杰燕于2009年3月3日和3月5日分别存入王保亮个人账户10.5万元和15.2万元,2009年3月6日由赵杰燕将王保亮个人账户上25.7万元转入童强项的个人账户。2009年3月9日账面上的支票存根仅反映划出95.5万元,无收款人及用途,账面挂“其他应收款-童国项”处理。银行留存的支票正联反映该款实际划入赵杰燕的个人账户,并于2009年3月10日由赵杰燕划入童强项的个人账户。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1000万元投资款中的186万元出资(增资)资金通过宝盛公司,利用财务处理上的虚假账户及支票存根内容与实际划账事实不相符的手法,掩盖资金真实流向,实际上已存在变相抽回的情况。盛德公司划入东驰公司的100万元,东驰公司账面反映为“长期借款”。2009年3月6日和同年3月10日,东驰公司分别提取现金4万元和45万元,支票存根用途写“还款”,账面处理为冲减“其他应付款-盛德公司”,银行留存的支票正联反映用途分别为“备用金”和“工资、奖金、差旅”。实际该两笔资金已于2009年3月6日和同年3月10日存入童强项的个人账户,东驰公司只是用虚假账务处理来掩盖资金的真实流向,实际上盛德公司已存在变相抽回49万元的情况。此外,盛德公司账面上反映开出四张支票划出资金共计170.9002万元,其中11万元支票为2009年2月26日归还童国英借款,45万元支票为2009年2月26日归还王保亮借款,90万元支票仅反映收款人为王保亮,未反映时间和用途,24.9002万元支票仅反映收款人为路神公司,未反映时间和用途。盛德公司账面均做冲减“其他应付款”处理,但未能查到以上四份支票在银行的支出记录。而在银行显示的是2009年2月27日盛德公司从兴业银行宁波海曙支行账号电汇170.9002万元至交通银行上虞支行企业账户。2009年3月11日童强项交通银行的个人账户上收到170.9002万元,与前述资金金额相符合。盛德公司划出的170.9002万元用虚假账户掩盖资金真实流向,实际上存在变相抽回出资(增资)资金的情形。综上,盛德公司在2009年2月26日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通过盛德公司及下属四家公司利用账面反映内容与资金流向及使用事实不符的虚假账务处理的方法,存在变相抽回出资(增资)资金共计915.9002万元,其中王保亮占股49%为448.7911万元。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绍天和专审字[2015]第002号司法鉴定审计报告显示,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经审计查证和多方面调查没有发现王保亮有返回出资(增资)资金的情况,王保亮对盛德公司2008年10月及2009年2月的两次出资(增资)存在变相抽回或抽回资金的情况共计868.7911万元。2008年12月16日,王保亮将其持有的奥德公司90%的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盛德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盛德公司同意用该135万元股权转让款抵冲王保亮从盛德公司抽回的部分增资资金,抵冲后王保亮实际应返还盛德公司资本本金733.7911万元。
2009年11月5日,梁子浩、王保亮签订《股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王保亮将其持有盛德公司49%的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梁子浩。同时还约定梁子浩在协议签订后7天内支付王保亮首期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并从2009年12月开始每月底支付王保亮23万元,至全部付清时止。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王保亮实际不再享有盛德公司的股东地位,王保亮确认至协议签订之日,盛德公司对于王保亮个人无未清偿债务,并承诺如今后发现盛德公司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对于王保亮个人负有债务的,王保亮自愿放弃其对盛德公司的债权。股权转让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分五期办理,首期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在梁子浩支付了100万元的当天签署完毕所需的法律文件,由盛德公司提交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所转让的股权份额为盛德公司10%的股权;第二期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在梁子浩按约支付12个月的股权转让款之后的10天内(2010年12月10日前)办理变更10%的股权;第三期在2011年12月10日前办理变更10%的股权;第四期在2012年12月10日前办理变更10%的股权;第五期在梁子浩按约支付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之后的10天内办理变更9%的股权。并约定,如梁子浩不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股权转让款,对于未按期支付的部分按照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支付利息,同时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时间相应顺延。如梁子浩有连续三期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王保亮可要求梁子浩一次性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股东协议》签订的当天,盛德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王保亮将其持有的盛德公司49%股权中的10%转让给梁子浩。协议签订后,梁子浩按约支付了王保亮首期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双方并于2009年11月12日办理了盛德公司1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2009年12月起,梁子浩在每月底向王保亮支付股权转让款23万元至2010年6月底,梁子浩共向王保亮支付股权转让款261万元。2012年12月12日,梁子浩又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上述合计支付361万元。
2012年6月12日,梁子浩与盛德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王保亮于2008年10月抽逃出资365万元,2009年2月至3月抽逃出资490万元,共计855万元至今未向盛德公司予以返还出资。经协商,盛德公司将855万元资金本息返还请求权全部转让给梁子浩,梁子浩应向盛德公司支付对价1040万元,该款项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个月内支付。2012年6月14日,盛德公司通过特快专递邮件向王保亮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关于债务抵销、协助办理公司登记变更手续的通知书,王保亮于2012年6月16日收悉上述材料。2012年11月2日,梁子浩分三次向盛德公司各汇款500万元、500万元、40万元,共计1040万元,梁子浩已履行了债权转让协议项下梁子浩的付款义务。
另查明,自2008年10月27日起至2012年6月16日(抵销之日)止,王保亮应返还盛德公司的资本本金为733.7911万元,应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的利息损失为159.0953万元,上述资本本息合计为892.8864万元。还查明,至2012年6月16日(抵销之日),梁子浩尚应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本金939万元,自2010年8月1日起至2012年6月16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分段计算的逾期利息66.8658万元,上述本息合计1005.8658万元。其中892.8864万元债务与王保亮应向梁子浩返还的892.8864万元出资本息抵销后,梁子浩尚应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本金112.9794万元。梁子浩于2012年12月12日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梁子浩尚应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本金12.9794万元。股权转让款本金112.9794万元自2012年6月17日至2012年12月1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的逾期利息为62863.62元。
上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第一,盛德公司对王保亮有无债权及其金额?该院认为,根据绍天和专审字[2015]第002号司法鉴定审计报告的审计查证,王保亮作为盛德公司的股东,在盛德公司第一次增资500万元的投资款到位后,用长期投资方法于2008年10月28日直接划入王保亮个人账户150万元,于2008年10月30日通过奥德公司划入王保亮个人账户270万元,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保亮与奥德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盛德公司在第二次增资1000万元的投资款到位后,在2009年2月26日至2009年3月11日期间,王保亮与其他股东通过盛德公司及下属四家公司,利用账面反映内容与资金流向及使用事实不符的虚假账务处理的方法,变相抽回出资(增资)资金共计915.9002万元。其中通过盛德公司本级划出资金170.9002万元,通过奥德公司划出310万元,通过奥星公司划出200万元,通过宝盛公司划出186万元,通过东驰公司划出49万元,其中王保亮占股49%抽逃资金448.7911万元。综上,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11月5日期间,王保亮对盛德公司2008年10月及2009年2月的两次出资(增资)存在变相抽回或抽回资金的情况共计868.7911万元。王保亮采取虚假账务处理、账面反映内容与资金流向及使用事实不相符等方法,掩盖资金真实流向,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可以认定其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王保亮辩称没有抽逃其在盛德公司的注册资本,但王保亮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资金转移系基于合法原因,亦未对注册资金的流向作出合理解释,对王保亮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王保亮作为盛德公司的股东抽逃出资,应当向盛德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盛德公司对王保亮享有出资本息返还请求权。因2008年12月16日,王保亮将其持有的奥德公司90%的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盛德公司,盛德公司同意用该135万元股权转让款抵冲王保亮从盛德公司抽回的部分增资资金。故截至2012年6月16日,盛德公司对王保亮实际享有733.7911万元资本本金及159.0953万元利息,合计892.8864万元资本本息返还请求权。
第二,盛德公司对王保亮是否负有债务?王保亮依据2007年7月盛德公司与奥德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合作协议》,辩称2007年盛德公司以500万元价款受让王保亮在奥德公司70%的股权,2008年10月盛德公司向王保亮支付股权转让款420万元,余款80万元未付。但根据奥德公司变更登记资料显示,2008年12月16日,王保亮作为奥德公司的股东,决定将持有的奥德公司90%的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盛德公司,另外10%的股权以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建华。同日,王保亮与盛德公司、黄建华三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向公司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时间、股权转让份额、股权转让价款等方面不一致,因2008年的协议已在公司登记管理部门进行了备案,具有公信力,故对王保亮将其持有的奥德公司90%的股权以135万元的价款转让给盛德公司的一节事实予以认定。此外,王保亮依据盛德公司2008、2009及2010年的审计报告中其他应付款项目的记载,称盛德公司尚欠王保亮应付款,但王保亮并未向提供债权凭证等证据加以佐证,亦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就其对盛德公司享有债权的事项进行司法审计鉴定,且根据2009年11月5日梁子浩与王保亮签订的《股东协议》,王保亮确认至协议签订之日,盛德公司对于王保亮个人无未清偿债务,并承诺如今后发现盛德公司至协议签订之日对王保亮个人负有债务的,王保亮自愿放弃其对盛德公司的债权,故截至2009年11月5日,盛德公司对王保亮不负有债务。
第三,盛德公司将其对王保亮的债权转让给梁子浩的行为是否有效?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王保亮作为盛德公司的股东抽逃出资,盛德公司享有请求王保亮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的权利。盛德公司与王保亮并未约定,相关法律亦未规定上述返还出资请求权不得转让。而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主要是指合同系基于特定当事人的身份关系订立,合同权利转让给第三人,会动摇合同订立的基础,使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盛德公司将其对王保亮的返还出资请求权转让给梁子浩,梁子浩已经支付盛德公司1040万元的对价,从公司法的原理来看,上述权利的转让并未损害盛德公司的合法利益,也未违反公司法有关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定,故盛德公司对王保亮的返还出资请求权不属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权利,盛德公司可以将该权利转让给梁子浩。梁子浩与盛德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王保亮于2008年10月抽逃出资365万元,于2009年2月至3月抽逃出资490万元,盛德公司对王保亮享有855万元资金本息返还请求权并将上述权利全部转让给梁子浩。可见盛德公司认为其对王保亮享有返还出资的本金为855万元,但根据前述第一个争议焦点所作的分析,盛德公司对王保亮享有的返还出资本金实际应为733.7911万元,故梁子浩受让的返还出资本息请求权限于资本本金733.7911万元及利息159.0953万元,合计892.8864万元。盛德公司将上述权利转让给梁子浩,已经依照法律规定通知了债务人王保亮,故上述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第四,股东协议项下梁子浩向王保亮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与依据债权转让协议王保亮对梁子浩所负的债务是否可以抵销?该院认为,抵销是指双方互负债务时,各以其债权以充当债务之清偿,而使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法定抵销是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具备时,以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抵销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本案中梁子浩发出抵销通知书时,虽然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尚未届至,但梁子浩自愿放弃期限利益,提前履行全部债务,未损害王保亮的合法权益,可以与王保亮的到期债务进行抵销。梁子浩以其对王保亮的返还出资请求权抵销梁子浩尚应支付王保亮的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定抵销的必备要件,且梁子浩已经依法通知了王保亮。梁子浩在抵销通知书中载明,至本通知发出之日,梁子浩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对王保亮享有债权本息共计1039.26万元,梁子浩基于《股东协议》对王保亮的全部付款义务为998.73万元,梁子浩要求抵销的金额为998.73万元。该院经审查,至2012年6月16日(抵销之日),梁子浩基于《股东协议》对王保亮的全部付款义务应为股权转让款本金939万元及利息66.8658万元,合计1005.8658万元。而梁子浩受让的盛德公司对王保亮的返还出资请求权为出资本金733.7911万元及利息159.0953万元,合计892.8864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债务抵销的金额为892.8864万元。至2012年6月16日即梁子浩抵销通知到达王保亮之日,892.8864万元债务抵销生效。上述债务抵销后,梁子浩尚应支付王保亮股权转让款112.9794万元,梁子浩于2012年12月12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还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12.9794万元、12.9794万元自2012年12月13日起的逾期利息及股权转让款112.9794万元自2012年6月17日至2012年12月12日的逾期利息62863.62元。在梁子浩完全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后,王保亮应当协助梁子浩办理盛德公司剩余39%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综上,梁子浩的诉讼请求,对其中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王保亮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股东协议》项下梁子浩对王保亮的8928864元付款义务与王保亮应支付给梁子浩的付款义务互相抵销,抵销金额为人民币8928864元;二、王保亮应在判决生效后梁子浩支付给王保亮股权转让款本息192657.62元及129794元本金自2012年12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的逾期利息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梁子浩办理《股东协议》项下剩余39%受让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三、驳回梁子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711元,由梁子浩承担7409元,王保亮承担74302元。一审鉴定费49400元,由梁子浩承担。重审鉴定费85000元、重审鉴定人员出庭费2000元,合计87000元,由王保亮承担。
王保亮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首先,一审法院在重新审理中依然存在诉审不一的严重错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和其法律关系必须保持一致。本案中梁子浩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0)绍虞商初字第2269号判决结案了。但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实际上审理的却是“债权抵销”和“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王保亮相信这也是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但一审判决对此避而不谈,更没有任何说理。其次,一审判决依然沿用错误的法律逻辑进行审理并对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1、关于“股东协议项下原告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与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被告对原告所负债务是否可以抵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当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梁子浩所谓的“债务”和王保亮的“债权”是否可以依法抵销?显然通过上面简单的文字表述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一审判决偷换概念,为了完成梁子浩所谓的“债务”和王保亮的“债权”抵销,富有创造性地将第三方的债权做了“技术转让”。从债务的标的物种类的统一性来看,一个是“尚未到期的股权转让款”,一个是“基于股东身份的出资返还债权”;而梁子浩要求抵销的还是“尚未到期的债务”。无论从哪一个条件来衡量债权抵销,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2、关于“盛德公司将其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的行为是否有效?”因为这是王保亮和盛德公司另外的法律关系和纠纷,本应当依法另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结合本案,首先应当确认的是“王保亮和盛德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王保亮与盛德公司之间是基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形成的股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除此之外,双方并无其他所谓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第28页作出了认定,一审判决没有就“梁子浩支付盛德公司1040万元对价的时间和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足足迟付了近半年”的客观事实进行考量和说理;盛德公司在没有收到梁子浩104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知王保亮“债权转让”?且不论该债权转让是否合法。一审判决仅从公司法的原理和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来考量盛德公司权利的转让并未损害盛德公司的合法利益,一审判决忽视王保亮还是持有盛德公司39%股权的股东身份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事人从签订《股东协议》之日起,所有的公司均在梁锡林和梁子浩掌控下经营。一审法院如果没有将上述客观因素放入案件中充分考量,凭什么认定“权利的转让并未损害盛德公司的合法权益”?再次,一审判决在案件发回重审中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和中立原则。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法应保持中立,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做到不偏不倚,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主张或放弃,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通过质证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子浩在(2012)绍虞商初字第2269号案件中,明确放弃了要求对涉案财务进行审计的权利。一审法院无视这一客观事实,在王保亮多次提出强烈异议的情况下,强行委托审计。更为重要的是,审计中涉及另外的法律关系,即盛德公司是否具有要求王保亮返还出资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另案处理。一审法院依据在违反上述诸多原则的情况下获得的《审计报告》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梁子浩的诉请。同时,王保亮以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诉请确认梁子浩与盛德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为由,向二审法院提交了案件中止审理申请书。
梁子浩在二审庭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不存在诉审不一的情况。一审法院审理围绕着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义务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来审理。本案一审判决也没有超过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也不存在所谓错误的法律逻辑。盛德公司与被上诉人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与抽逃出资返回义务同属义务,不为法律禁止抵销,梁子浩放弃期限利益,主张抵销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在另一案件中放弃审计不意味在本案中也放弃审计权利,梁子浩在一审中要求审计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王保亮滥用诉讼权利,在本案尚未审理终结时,就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股权转让是本案讼争焦点之一,王保亮在海曙区人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冲突,请二审法院与海曙区人民法院协调。王保亮要求法院中止审理的申请不成立。综上,请求依法尽快驳回王保亮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案由应否为股权转让纠纷;二是一审法院委托审计是否妥当,审计报告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三是盛德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四是债权受让人梁子浩是否可向王保亮主张债务抵销。对此分别评判如下:
一、本案案由应否为股权转让纠纷。王保亮主张(2010)绍虞商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已经就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作出认定,而本案实际审理的却是债权抵销和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与确定的案由股权转让纠纷不符。(2010)绍虞商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系梁子浩以受欺诈为由要求撤销与王保亮2009年11月5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但梁子浩的诉请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现梁子浩起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同时要求王保亮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仍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一审确定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并无不当。梁子浩主张系以债务抵销方式履行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故一审势必需要审查债权转让及债务抵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诉审不一的情况。
二、一审法院委托审计是否妥当,审计报告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王保亮提出双方在(2010)绍虞商初字第226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均未要求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本案不能再行审计。该案系梁子浩以盛德公司资产不实为由请求撤销《股东协议》,主张王保亮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形,但在该案中是否委托审计系梁子浩根据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后的决定,梁子浩在该案中不要求对公司资产进行审计并不意味着在本案中不能申请司法审计。正如王保亮所辩称,盛德公司转让债权的前提是盛德公司对其享有债权。现盛德公司转让给梁子浩之债权系盛德公司要求王保亮返还出资之债,据此,王保亮是否存在抽逃出资即为问题的关键。为查明该节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梁子浩的申请委托专业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计机构依法出具的审计报告依法应当作为认定王保亮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依据。
三、盛德公司的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关于盛德公司对王保亮的出资返还债权能否转让问题。王保亮提出盛德公司与其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但并非只有合同之债才能转让,从现有法律规定看,并未有明文禁止公司转让出资返还债权。盛德公司将返还出资权进行转让,获得的对价用以补充公司资本,有利于公司更及时地填补资本,并不损害公司利益,故应当认定盛德公司的债权转让有效。此外,王保亮提出盛德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梁子浩时未通知他,且梁子浩在支付转让款之前即将债权转让通知寄送给王保亮。二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股东协议》中已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即王保亮)实际不再享有盛德公司的股东地位”,据此,盛德公司将出资返还债权进行转让并不需要征得王保亮的同意。另外,梁子浩实际支付债权转让款的时间并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故债权转让通知到达王保亮时即生效。
四、债权受让人梁子浩是否可向王保亮主张债务抵销。本案梁子浩对王保亮负有支付《股东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的债务,王保亮应当向债权受让人梁子浩支付出资款,双方互负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王保亮与梁子浩的债务均为金钱债务,梁子浩主张抵销符合法律规定,梁子浩受让债权时部分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期限尚未届至,梁子浩放弃期限利益一并主张抵销并不损害王保亮的利益,抵销有效。
对于王保亮申请本案中止审理的问题。王保亮请求确认梁子浩与盛德公司之间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一案虽已由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受理,但本案受理在先,且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已包含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故王保亮的申请事项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对于王保亮提出的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
另外,双方在《股东协议》中第四条关于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事项约定分五次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梁子浩支付了12个月的股权转让款(即每月23万元)之后的10天内办理10%的股权变更登记;梁子浩支付了24个月的股权转让款后的10天内办理10%的股权变更登记;梁子浩支付第36个月的股权转让款后的10天内办理10%的股权变更登记。根据现在梁子浩的支付情况,股权转让款第二、三、四次股权变更登记条件已成就,王保亮应当协助梁子浩对相应30%的股权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对于剩余9%的股权,梁子浩应支付完剩余股权转让款后方才可以要求王保亮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一审判决王保亮在梁子浩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后协助办理变更登记,并无明显不当。因王保亮在一审时并未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提起反诉,故梁子浩何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在本案中未作出处理,故一审判决第二项中所涉利息应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综上,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5)绍虞商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5)绍虞商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王保亮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梁子浩办理《股东协议》项下30%受让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四、王保亮应在判决生效后梁子浩支付给王保亮股权转让款本息192657.62元及129794元本金自2012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计算的逾期利息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被上诉人梁子浩办理《股东协议》项下剩余9%受让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五、驳回梁子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711元,由梁子浩负担7409元,王保亮负担74302元。原审鉴定费49400元,由梁子浩承担。重审鉴定费85000元(已由梁子浩预缴),重审鉴定人员出庭费2000元(已由王保亮预缴),合计87000元,由王保亮承担(由梁子浩预缴的重审鉴定费85000元,由王保亮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梁子浩)。二审案件受理费81711元,由王保亮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王保亮提供了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盛德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明盛德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变更至10万元,所谓梁子浩支付的1040万元对价系虚假,进一步证明本案诉讼就是梁子浩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资产。梁子浩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证明对象和内容与案件审理的关联性有异议。工商登记记载的10万元,只是对公司变更登记后注销时在册登记股东注册资本的描述。该份证据与本案再审的双方就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中债权抵销问题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梁子浩没有新证据提供。
本院对王保亮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鉴于梁子浩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证明效力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再审查明:盛德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8日,2017年4月11日,该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注销登记。工商登记材料显示盛德公司注销前的注册资本金为10万元。其他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根据王保亮提出的再审理由及梁子浩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
一、关于原判认定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有无不当。王保亮再审认为,原判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错误。经查,梁子浩系依据其与王保亮签订的股东协议,诉请确认股权转让款已支付,要求王保亮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由于案由是案件的内容提要,是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的集中概括,当事人虽在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涉及抵销的事实,但仍以《股东协议》作为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的基础事实,双方基于股权转让而发生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办理股权过户的纠纷,原判将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并无不当。
二、关于梁子浩主张债务抵销依据是否充分。梁子浩一审诉请确认其于股东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已经与王保亮对梁子浩的债务进行抵销。因此,本案除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还涉及盛德公司与王保亮之间的返还抽逃出资法律关系以及盛德公司与梁子浩的债权转让关系等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规定,法定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同种类额债务,且债务均已借清偿期的,为使相互间所负相当额至债务同归消灭的一方意思表示。法定抵销必须具备:⑴当事人互负债务,互享债权。⑵抵销的债务必标的物相同、品质相同。⑶必须双方债权均届清偿期。⑷双方债务必须均非按照合同的性质或者依照法律不得抵销的债务。结合本案,梁子浩一审起诉主张其支付给王保亮的股权转让价款与其受让盛德公司对王保亮返还抽逃出资的请求权已予以抵销。经查,梁子浩与王保亮签订《股东协议》时,盛德公司股东为王保亮和梁子浩的父亲梁锡林,而梁锡林为盛德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0)绍虞商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认定,王保亮与梁子浩签订《股东协议》前夕,梁子浩带专业律师在盛德公司财务总监的陪同下,对盛德公司及其控股的四个子公司进行了考察,故有理由相信梁子浩在股权受让前对盛德公司及其控股的四个子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等有较详细的了解。同时,案涉股权转让协商之初,王保亮也曾提出过以960万元受让梁锡林51%的股权,双方均有受让对方股权的意向,存在一个询价、磋商基础,股权转让有一个竞价过程。而根据审计报告,盛德公司在两次增资的过程中,公司股东王保亮与梁锡林均存有抽逃出资的行为,故梁子浩在受让王保亮的股权时,应当知道王保亮抽逃出资的情况。因此,王保亮提出的本案《股东协议》约定的1200万元转让价款系股权净价的主张更具合理性。梁子浩受让王保亮股权后,依法负有向盛德公司补足王保亮抽逃出资部分的义务。其次,盛德公司从2009年11月6日始,该公司实际由梁子浩、梁锡林父子俩控制。梁子浩提起的《股东协议》确认无效诉讼被法院于2012年6月1日终审判决驳回后,盛德公司与梁子浩于2012年6月12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盛德公司以股东梁子浩支付1040万元的价格转让公司对王保亮返还抽逃资金855万元请求权。在股东之间具有亲属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梁子浩再以1040万元的代价受让盛德公司对王保亮的855万元的返还抽逃出资请求权,明显不符情理。最后,结合工商登记记载的盛德公司注销前注册资本金已减到10万元,而对于梁子浩支付给盛德公司的1040万元受让返还抽逃注册资本的请求权款项去向,梁子浩根据法庭的要求在庭审后提供证据,由盛德公司借给了案外人浙江大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而梁子浩在再审庭审中陈述,盛德公司从2009年11月至注销没有开展业务,因此两者明显存有矛盾。综上,梁子浩主张本应由其承担的盛德公司注册资金补足义务与其应支付给王保亮的股权价款进行抵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法定抵销条件,梁子浩提出的抵销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王保亮是否存有抽逃出资的行为。王保亮认为,原判认定其存有抽逃资金依据不充分。经查,本案经二次审计鉴定,原判认定事实依据的鉴定结论,系由具有法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亦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王保亮虽提出鉴定机构鉴定时的资料不齐全,但未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绍兴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绍天和专审字[2015]第002号司法鉴定审计报告显示,盛德公司第一次增资的500万元存在变现抽回或抽回资金情形,王保亮抽回420万元,梁锡林抽回80万元;盛德公司第二次增资的1000万元,王保亮抽回448.7911万元,梁锡林抽回467.1091万元。现王保亮不能提供证据推翻上述鉴定结论,原判认定王保亮存有抽逃出资有相应依据。当然,本院也注意到,因梁子浩与王保亮签订的《股东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系净价,王保亮抽逃注册资金的款项理应由梁子浩补足,故王保亮抽逃出资的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同时,梁子浩和梁锡林两个股东将盛德公司注册资金从2000万元减资至10万元,若盛德公司有盈余且对外无负债时,梁子浩和梁锡林从公司取得财产的行为,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鉴于梁子浩提出的债务抵销的主张依据不充分,梁子浩一审的诉请不予支持,故本案的其他争议焦点已无需再赘述。
综上,王保亮提出的梁子浩主张债务抵销依据不充分的再审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他理由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终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终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驳回梁子浩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17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711元,一审鉴定费49400元,重审鉴定费85000元、重审鉴定人员出庭费2000元,均由梁子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玲丽
审 判 员 樊清正
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
张章生诉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再审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浙民再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章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江文,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芝瑛,系张章生妻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宇,系公司董事。
再审申请人张章生因与被申请人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缝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浙民申4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再审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培良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梅冰、代理审判员王雄飞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本案。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章生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江文、周芝瑛,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姚善挺、冯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中缝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向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2004年1月6日,张章生与胡浩亮、曾华利、香港伟昌衣车有限公司、日本ASAHISEWINGMACHINECO.LTD、日本WORLDONECO.LTD六方共同出资设立宁波中缝公司,注册资本5010000美元。按中缝公司公司章程的约定,张章生认缴的出资为1603200美元,占注册资本的32%,且应于该公司注册成立前全部到位。外方股东的出资在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分期到位。2004年1月5日,经宁波雄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张章生履行了全部的出资义务。但根据股东内部决议,中方股东的出资可与外方股东的出资同步到位,即宁波中缝公司同意张章生抽回部分注册资本。期间,张章生通过其个体经营的长谊缝纫机店和其在乐清市中缝伟业缝纫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清伟业公司),借离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14016510元。但张章生在借离注册资本后未能及时归还全部借离款,至今仅归还人民币9636510元,尚有人民币4380000元挂账处理在乐清伟业公司预付款项下。2009年7月16日,宁波中缝公司曾向北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张章生归还上述注册资本金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北仑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以张章生有抽逃出资犯罪嫌疑,应由公安机关处理为由,驳回中缝公司起诉。后张章生不服上诉至宁波中院,宁波中院认为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抽逃出资,通过其在浙江乐清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做挂账处理,其行为有经济犯罪嫌疑,驳回了张章生的上诉。2013年12月4日,北仑公安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认为张章生虽有抽逃注册资本金的事实,但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有关经济纠纷事宜,法院依法继续处理。中缝公司认为,张章生作为公司股东和副董事长,利用公司准许其与外资同步到位的承诺,在借离注册资本后,未能在约定时间归还。请求判令:张章生返还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并支付自2007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张章生在一审中答辩称:其已于2004年12月10日完成了全部出资义务,共出资1603200美元。涉案人民币4380000元与注册资本金无关,系中缝公司与张章生之间的业务往来款。2009年7月16日,中缝公司曾以相同事实理由向北仑法院提起诉讼,该诉讼终结后中缝公司从未针对该人民币4380000元向张章生主张权利,故本次诉讼是重复诉讼,法院不应受理,且中缝公司本次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中缝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2003年12月,张章生与案外人胡浩亮、曾华利、香港伟昌衣车有限公司、日本ASAHISEWINGMACHINECO.LTD、日本WORLDONECO.LTD订立合资经营合同,约定共同出资设立中缝公司,公司注册资金5010000美元。公司章程规定张章生认缴额为1603200美元,占注册资本32%,合资公司注册成立之前,张章生以及胡浩亮、曾华利的出资应全部到位,其他投资方的出资在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分期到位,等等。2004年1月5日,经宁波雄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张章生实缴人民币13269910元,其认缴的人民币13269526.08元注册资本全部到位。同年1月6日,中缝公司成立。针对注册资本到位问题,股东内部达成协议,中方股东注册资本可与外方股东注册资本同步到位。中缝公司与张章生之间涉讼款项具体往来如下:2004年1月13日,中缝公司通过银行向北京市大红门长谊缝纫机修理店(以下简称长谊缝纫机店)汇款两笔,一笔人民币1260000元,另一笔人民币3380000元;同年3月1日,中缝公司通过银行向长谊缝纫机店汇款人民币1000000元。该店系以张章生为业主的个体工商户,已于2006年5月12日注销;2004年6月6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出具借条两份,分别借款人民币3000000元和人民币2000000元;2004年7月14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出具借条一份,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2004年7月16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借款人民币206600元;同年10月11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出具借条一份,借款人民币116991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14016510元。此外,张章生于2004年8月16日归还中缝公司人民币2760000元,于同年10月5日归还人民币6600元,于同年12月10日归还人民币6869910元,合计人民币9636510元。张章生借离款项与归还款项差额为人民币4380000元(计算公式:14016510元-9636510元)。2004年6月8日,上述差额人民币4380000元在中缝公司的账面上由长谊缝纫机店的其他应收款转为中缝公司支付给乐清市中缝伟业缝纫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清伟业公司)的预付账款。2006年12月,外方股东出资全部到位。2009年7月16日,中缝公司曾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张章生返还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北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章生有抽逃出资犯罪嫌疑,本案不属于商事纠纷,应由公安机关处理,故于2010年3月25日作出(2009)甬仑商初字第137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中缝公司起诉。张章生对该裁定不服上诉至宁波中院,宁波中院审理后认为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抽逃出资,通过其在浙江乐清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做挂账处理,其行为有经济犯罪嫌疑。故于2010年5月26日作出(2010)浙甬商终字第457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第457号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3年12月4日,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北仑公安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经调查,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虽有抽逃注册资本金的事实,但鉴于未造成严重后果和考虑社会和谐稳定,故不立案侦查,相关经济纠纷事宜,可由法院依法继续处理。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章生以其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在中缝公司采取人民币4380000元预付账款挂账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上述款项挂账后,乐清伟业公司向中缝公司供货的应收货款能否视为张章生返还的出资。二、中缝公司起诉是否系重复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中缝公司认为该人民币4380000元系张章生抽逃的出资,应予以返还。该人民币4380000元原系张章生通过其个体经营的长谊缝纫机店从中缝公司处抽离的款项,2004年6月8日,在中缝公司的账面上该款项由长谊缝纫机店的其他应收款转为中缝公司支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预付账款,但中缝公司从未向乐清伟业公司实际支付过该笔款项,张章生亦未支付,该人民币4380000元是挂账处理在乐清伟业公司预付款项下的。之所以做挂账处理,一方面是因为股东内部存在中方股东出资可与外方股东出资同步到位的约定,另一方面上述约定有违法律规定,为了掩盖其非法性,使中缝公司能通过年检,所以在账面上进行了处理。虽然中缝公司与乐清伟业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中缝公司从未认可该人民币4380000元可以通过乐清伟业公司供货的货款予以归还、冲抵,中缝公司与乐清伟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另行结算。张章生认为,2004年12月10日,张章生已全额履行了出资义务,该人民币4380000元系中缝公司支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预付款,该款项在乐清伟业公司持续的供货过程中不断减少,证明中缝公司已认可该款项的性质为预付款,并非张章生抽逃的出资。该院分析认为,第一,中缝公司于2004年1月6日注册成立,2004年1月13日至3月1日中缝公司即向张章生个体经营的长谊缝纫机店汇款人民币5640000元,虽然汇款凭证上款项用途载明的是货款、往来款,但中缝公司与长谊缝纫机店之间并不存在相关业务往来。2004年6月6日至10月11日,中缝公司又陆续向张章生出借款项共计人民币8376510元,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如此连续、大额的向中缝公司借款也不符合正常借款的特征。上述人民币14016510元款项(计算公式:5640000元+8376510元)流转的特征反而能与中缝公司股东内部关于中方股东出资可与外方股东出资同步到位的约定相契合。同时,北仑公安局经调查后认为,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存在抽逃注册资本金的事实,故张章生从中缝公司处获得的上述共计人民币14016510元款项均系张章生抽逃的出资,后张章生陆续归还人民币9636510元,还余人民币4380000元至今未还。2004年6月8日,在中缝公司的账面上该人民币4380000元由长谊缝纫机店的其他应收款转为中缝公司支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预付账款,但该款中缝公司、张章生均未向乐清伟业公司实际支付,系挂账处理。该挂账行为,没有改变张章生通过其经营的长谊缝纫机店抽逃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的本质,仅改变了张章生抽逃出资的形式。对此,该院作出的(2009)甬仑商初字第1377号民事裁定及宁波中院作出的第457号裁定中均认定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通过其在浙江乐清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做挂账处理,系抽逃出资。第二,中缝公司从未认可张章生返还出资的义务转由乐清伟业公司承担,并同意以应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货款予以冲抵。虽然该人民币4380000元已挂账至乐清伟业公司预付账款项下,如张章生不归还该笔款项,从账面上看,该款必然会与之后中缝公司与乐清伟业公司实际交易的款项发生冲抵。因中缝公司股东内部约定中方股东出资可与外方股东出资同步到位,外方股东出资全部到位时间为2006年12月,在此之前,为掩盖张章生抽逃出资的事实,中缝公司在账面上亦会持续冲抵该人民币4380000元。故不能仅以账面上该人民币4380000元不断被应付乐清伟业公司的货款冲抵、减少而推出中缝公司已同意张章生用上述债务转移的方式返还已抽逃的出资。第三,张章生返还人民币4380000元出资的义务不能转移。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与股东以其出资份额所享有的权益是对等的。股东的出资义务与股东身份相伴而生,具有一定的身份属性,该出资义务不能随意转移。综上,该院认为张章生以其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在中缝公司采取人民币4380000元预付账款挂账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上述款项挂账后,乐清伟业公司向中缝公司供货的货款不能视为张章生返还的出资。中缝公司与乐清伟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可另行理直。关于争议焦点二,中缝公司认为其起诉并非重复起诉且未超过诉讼时效,张章生认为中缝公司基于相同事实理由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同时张章生已于2004年1月5日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中外股东出资同步到位的约定,张章生最晚也应在2007年1月完成出资义务。中缝公司于2009年7月向法院起诉要求张章生返还出资已超过诉讼时效。现中缝公司再次向法院起诉,亦不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该院认为,虽然中缝公司曾于2009年7月16日向本院起诉要求张章生返还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但该院及宁波中院经审理后均认为张章生有抽逃出资犯罪嫌疑,并将上述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后北仑公安局经调查后认为,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虽有抽逃注册资本金的事实,但鉴于未造成严重后果和考虑社会和谐稳定,故不立案侦查,相关经济纠纷事宜,可由法院依法继续处理。现中缝公司再次向该院起诉并非重复诉讼。同时,中缝公司要求张章生返还人民币4380000元出资的请求权是基于股东的法定出资义务而由公司享有的法定债权请求权,不同于基于当事人合意产生的意定债权请求权,公司的资本必须充足否则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也不利于其他足额出资的股东及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护。故上述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张章生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该院难以支持。综上,该院认为,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抽逃出资,中缝公司有权要求其返还出资本息。中缝公司诉请正当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张章生的答辩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该院难以采信。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年修订)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8日作出如下判决:张章生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中缝公司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并支付自2007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张章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898元,由张章生负担。
张章生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根据中外股东出资同步到位的约定,张章生可以保留与外方股东同比例的注册资本金,退出超出部分注册资本金。张章生退出部分注册资本金后又以现金方式归还人民币9636510元,完成了注册资本金义务。双方自2004年成立至2008年合作期间,从未就股东出资问题发生纠纷。中缝公司不顾张章生缴纳人民币13269910元后保留与外方股东同比例注册资本金的事实,混淆中缝公司与张章生及关联公司的人民币14016510元往来款项性质,并断章取义地将该款项减去人民币9636510元的人民币4380000元称作未出资。本案证据充分表明,张章生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2004年4月21日,中缝公司全体董事签署《各股东投资额清算说明》,中缝公司及全体董事盖章签字一致确认,截至2004年4月21日,张章生已实际出资人民币5100000元。2004年12月6日,中缝公司及各董事签订的《股东增资计划》和《股东实际到位股金》,中缝公司及全体董事盖章签字一致确认,截至2004年12月6日,张章生实际出资人民币6400000元。2004年12月10日,张章生汇入中缝公司总计人民币132699010元,即严格履行了出资义务,对此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并非根据证据认定事实,而是根据设定好的事实而否定证据,明显认定事实错误。涉案人民币4380000自始不存在,是中缝公司在双方合作破裂后杜撰得出,且该人民币4380000元已经结清。2004年1月13日,中缝公司与长谊缝纫机店款项往来发生两笔,分别为人民币1260000元和人民币3380000元,且汇款凭证中明确是中缝公司对长谊缝纫机店“货款”,同年3月1日,中缝公司与长谊缝纫机店往来款人民币100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人民币5640000元。2004年6月8日,中缝公司记账凭证中,将该款项转为乐清伟业公司,明确预付款人民币5680000元,张章生签署的领款收据明确为预付公司货款。上述凭证均保存在中缝公司财务账册中,是当时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的书证,2004年6月8日预付货款共人民币5680000元,自始至终未出现人民币4380000元,中缝公司仅主张其中的人民币4380000元是出资款且未缴纳,而不解释另外人民币1300000元,无任何事实依据。此外,根据2004年至2006年中缝公司会计报表附注,乐清伟业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从人民币6365418.33元逐年减少,分别为2005年的人民币4004266.16元、2006年的人民币1669892.81元。中缝公司自称人民币4380000元被包括在乐清伟业公司人民币6365418.33元中,但该余额到2006年仅剩余人民币1669892.81元,截至2007年仅剩余人民币743436.31元(人民币400000元设备款未计入),明显不存在欠付人民币4380000元的事实。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是中缝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而非乐清伟业公司或张章生杜撰。扣除人民币400000元设备款,预付款余额仅有人民币343436.31元。综上,既然中缝公司认为人民币4380000元是预付货款挂账,而又不认可供货导致该金额减少,原审法院认定中缝公司从未认可张章生返还出资的义务由乐清伟业公司承担,并同意以应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货款予以冲抵,明显与上述基本证据相悖,根本错误。自2004年1月至2009年7月16日前,中缝公司从未向张章生主张人民币4380000元是注册资本金,更未向张章生主张还款人民币4380000元。现中缝公司提出该主张有悖常理及基本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中缝公司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
中缝公司答辩称:张章生以其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在中缝公司采取人民币4380000元预付账款挂账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经过一审法院、宁波中院以及北仑公安局的认定,事实清楚。张章生通过长谊缝纫机店在中缝公司抽逃出资到其名下,未通过任何形式将该款交付乐清伟业公司,然而乐清伟业公司虽未收到该笔款项,却仍然做了挂账处理,明显系抽逃出资。根据当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中方股东出资必须一次性到位,并不是所有股东内部同意就可以抽逃出资。另外,已挂账处理的人民币4380000元在账面上逐渐减少,只是为了平账需要,中缝公司从未认可过该款项与乐清伟业公司的货款相抵扣。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第457号裁定已认定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抽逃出资,通过其在浙江乐清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做挂账处理。北仑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又已认定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抽逃出资。因此,张章生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事实是明确的。关于张章生抽逃出资的数额,双方存在争议。中缝公司认为,张章生通过长谊缝纫机店从中缝公司抽逃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该款项在中缝公司账面上转为中缝公司支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预付账款。张章生认为,该人民币4380000元并不存在,相关财务凭证记载2004年6月8日中缝公司预付货款人民币5680000元,至始至终未出现人民币4380000元这一数字,如认为4380000元以预付货款形式挂账处理,但该款项又在乐清伟业公司的供货过程中不断减少,截至2007年仅剩余人民币743436.31元,证明该款项性质为预付款。该院认为,张章生及其个体经营的长谊缝纫机店以借款或汇款形式从中缝公司取得款项共人民币14016510元,归还款项共人民币9636510元,两者相减差额为人民币4380000元。2004年6月8日,该人民币4380000元款项在中缝公司的账面上由长谊缝纫机店的其他应收款转为中缝公司支付给乐清伟业公司的预付账款。至此,张章生通过预付款挂账形式抽逃出资人民币4380000元。虽然乐清伟业公司与中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挂账的预付款在账面上也在乐清伟业公司与中缝公司的实际交易中逐渐减少,但因中缝公司、张章生均未向乐清伟业公司支付过该款项,乐清伟业公司实际未收到该预付款,而乐清伟业公司、中缝公司之间与中缝公司、张章生之间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缝公司关于其账面上该款逐渐减少只是为了平账需要符合常理,其从未认可该人民币4380000元可与乐清伟业公司的货款相抵扣,故即使已挂账的预付款在账面上逐渐减少,也不能即由此认定中缝公司同意两笔款项相抵扣。至于中缝公司与乐清伟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可另行理直,本案中不宜处理。综上,张章生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难以支持。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898元,由上诉人张章生负担。
张章生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证据充分表明,张章生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004年4月21日,宁波中缝公司全体董事签署《各股东投资额清算说明》,宁波中缝公司及全体董事盖章签字一致确认,截止2004年4月21日,张章生已实际出资510万元。2004年12月6日,宁波中缝公司及各董事签订的《股东增资计划》和《股东实际到位股金》:宁波中缝公司及全体董事盖章签字一致确认,截止2004年12月6日,张章生实际出资640万元。(二)涉案438万自始不存在,是宁波中缝公司在双方合作破裂后杜撰得出,且该438万元已经结清。2004年1月13日,宁波中缝公司与中缝公司款项往来发生两笔,分别为126万元和338万元,且汇款凭证中明确是宁波中缝公司对北京长谊公司“货款”;3月1日,宁波中缝公司与北京公司“往来款”100万;上述款项共计564万元。2004年6月8日,宁波中缝公司记账凭证中,将该款项转为乐清公司,明确预付款568万元,张章生签署的领款收据明确“预付公司货款”。上述凭证均保存在宁波中缝公司财务账册中,是当时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的书证;2004年6月8日中预付货款共568万元,自始自终未出现438万元,宁波中缝公司仅主张其中的438万元是出资款且未缴纳,而不解释另外130万元,无任何事实依据。此外,根据2004年至2006年宁波中缝公司会计报表附注,乐清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从6365418.33元逐年减少,分别为2005年的4004266.16元、2006年的1669892.81元。宁波公司自称438万元被包括在乐清公司6365418.33元中,但该余额到2006年仅剩余1669892.81元,截止2007年仅剩余743436.31元(40万元设备未计入),明显不存在欠付438万元的事实。上述是宁波中缝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而非乐清公司或被告杜撰。(三)宁波中缝公司主张,存在诸多违背常理、违背基本事实之处。张章生从宁波中缝公司借出资金,是全体股东及董事一致同意的。根据一审法院认定,在张章生出资后至张章生第一次归还现金,张章生共借出款项及货款共计12846600元,与注册资本金13269910元仅差423310元,与外方股东出资明显不同步;张章生2004年7月16日借出款项及2004年8月16日、10月5日归还款项均非整数,明显是根据各股东测算的应归还款项得出,宁波中缝公司未提供完整证据对此进行解释。(四)关于本案的其他事实。张章生自2004年出资13269910元后,特别是2008年双方合作破裂后,无法参与、决策公司的经营管理及一切事宜。宁波中缝公司以股东投资到公司的资金屡次提起诉讼,并将公司土地及厂房对外出租获得权益,而张章生未收回任何投资。原审判决除认定事实错误之外,在法律适用及法律推理上亦存在明显逻辑错误。请求:一、依法撤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4)甬仑商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880号民事判决;二、依法驳回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承担。
宁波中缝公司辩称:应支持中缝公司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1)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抽逃出资,通过乐清伟业公司挂帐的形式抽逃出资,这也已被生效判决确认(2010年3月5日北仑法院1377号民事裁定、2010年5月26日宁波中院作出的457号民事裁定以及省高院2010年706号民事裁定)。关于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故对该事实,被申请人无需举证。北仑法院认定张章生违反公司法规定,抽逃出资超过50万元,且股东存在合谋出资的可能。宁波中院进一步确认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规定抽逃出资,通过其设立的乐清伟业公司作挂帐处理,属抽逃出资。这两份生效文书已经明确确认其以乐清伟业公司挂帐形式抽逃出资。(2)本案再审审查范围仅限于北仑法院2014年243号判决书和宁波中院2015年830号的判决书,而不及于第一点中所提到的3份生效法律文书。(3)张章生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也经过了宁波公安北仑分局的侦查,据公安向北仑法院反馈的书面反馈文件,也认为张章生有抽逃出资的行为,只是认为年份已久,无重大后果,故未予处理。(4)北仑公安对张章生进行了询问,张章生明确强调其注册资本金在帐面上是一直到位了,只是业务未尽。关于再审申请人在再审中提出的崭新观点,属新的事实,在双方长达9年的诉讼中,张章生始终认为其出资全部是以现金出资,从未主张过以设备出资。故再审申请人在现在提出不能得到支持。(5)关于438万元的问题。根据相关证据以及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438万元是通过乐清伟业公司的名义作挂帐处理,乐清伟业公司从未收到过张章生438万元款项,中缝公司股东合谋将张章生抽逃出资的438万元以预付货款的形式所作的。中缝公司股东合谋后,张章生以借款等形式向中缝公司陆续借得款项1401万元,张章生主张其仅出资1300万元,不可能借款1401万元,但结合时间节点,张章生累计归还的963万元,其余进入了乐清伟业公司的帐户。之前的诉讼中张章生表示乐清伟业公司从未收到过该笔款项。568万元的一张收据,因为此前在原审提交过说明。438万元挂帐到乐清伟业公司时,中缝公司已预付乐清伟业公司130万元的货款。当时股东合谋将张章生其中的438万元连通实际已收的130万元,故产生568万元的收据。由于有股东合谋的事实,相关文件应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重新审查。对于张章生是否抽逃出资的问题。不能以股东允许其抽逃出资的方式进行认定,不能因为股东合谋或者同意抽逃出资,也不能视为抽逃出资合法或者不构成抽逃出资。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抽逃出资后应否归还,也应以公司法规定来处理,而张章生至今未予返还。(6)本案相关证据,再审申请人已在原来相关诉讼中进行过披露,对股东实际到位股金以及张章生、周芝瑛的情况说明的证据,原审已经出现。实际出资额只是证明1300万元验资时,其筹集的金额是1300万元,而不能据此认定其1300万元实际已到位。中缝公司认为原审判决正当,请求予以维持。
再审中,张章生提交了七份证据材料,证据1:2003年12月18日《建立合资经营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合同》,证据2:2003年12月22日《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章程》,证据3:2005年4月30日《建立合资经营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合同》,证据4:2005年4月30日《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章程》,证据5:2003年12月25日《关于中外合资宁波中缝缝纫机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证据1-5拟证明:张章生出资方式应为现金出资和设备出资,宁波中缝公司在2003年的合资合同即章程中变更了张章生出资形式,张章生实际以货币形式出资,将“设备”部分变更为张章生与宁波中缝公司之间买卖关系,为了与开发区批复保持一致,宁波中缝公司在2005年4月30日备案的章程及合同中对张章生的出资形式进行更正。证据6:2004年9月19日《股东实际到位股金》,拟证明:宁波中缝公司2014年9月19日确认,张章生实际到位股金640万元,与张章生一审证据1内容相互印证。该640万元与张章生2004年12月10日归还中缝公司的6869910元,合计13269910元即出资款,与验资报告数额完全一致。证据7:张章生、周芝瑛的情况说明,拟证明乐清伟业公司实际收到438万元预付货款。
宁波中缝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2,我方在原审中作为证据提交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对证据1、3、4,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与在宁波工商局北仑分局批复内容不一致,该批复是中缝公司设立时的第一份批复,原件留存在北仑工商局档案室,留存的批复已经修改,也加盖了相关印章。退一步讲,即便设备出资和现金出资,也未有设备的验资报告。对证据1、3、4、5,对再审申请人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即便章程和合同进行了修订,但是按照再审申请人证据反映,修正的时间点是2005年,而中缝公司成立至2003年底2004年初,在成立时张章生的出资也已一次性到位。此后即使按照2005年修改的章程以及合营合同,也未明确货币金额多少,设备出资多少。故原验资款1300万元是以现金出资。若之后调整为设备出资加现金出资,那也应当将设备评估作价,也应以设备的验资报告作为其作价入股流程,但未有设备的验资报告。且对设备出资也是张章生最新的说法,也与此前的陈述相互矛盾。对证据6形式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以及证明内容都有异议。这份材料出具时间是2004年9月19日,张章生在2004年1月份表面的出资额是1300万元,但此时张章生的借款金额是有据可查的。按照实际股金是640万元。在2004年9月份至2004年12月份,存在借、抽逃出资、归还、借、抽逃出资的款项往来,在2004年9月19日实际股金是640万元,而3个月之后还是640万元,这是不可能的。结合各股东在北仑工商局所作的笔录,真实的意思是当时在2003年底张章生实际到位资本,而并未结合有没有抽离等因素。根据各投资额说明,张章生出资510万元,加上另外二人的100万元和200万元,这也与2004年9月19日的实际股本是一致的,仅是指1326万元张章生实际本人出资投入的对应金额是640万元。在2004年12月6日再次确认张章生的验资款是640万元,而并非张章生只抽逃700多万元,还有640万元的意思。对合法性有异议的原因是北仑法院和工商局对中外股东约定的同步到位认定中外股东合谋抽逃出资。对于股东认可的出资金额,应结合事实数据来看。故不能证明到2014年9月19日张章生未抽逃出资的股本金是640万元。对证据7,乐清伟业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此前庭审中张章生及其代理人明确陈述“没有把从中缝公司借到的钱中的438万元给过乐清伟业公司,中缝公司未收到过该438万元”(见二审法院庭审笔录,二审判决书第7页第8行),故乐清伟业公司有没有收到过438万元有据可查,宁波中院二审对此认定有事实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证据2已经由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供,不属于再审新证据。证据1、3、4,被申请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资格予以确认。证据5,被申请人对真实性有异议,结合宁波中缝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验资报告(证明2004年1月5日,张章生出资1603200美元全部到位),以及被申请人的质证意见,再审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据1、3、4、5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被申请人对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各方股东认可2004年9月19日,张章生实际到位股金640万元。证据7,虽然被申请人不予认可,但作为乐清伟业公司股东的张章生、周芝瑛均出庭,结合被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交的领款收据,能够互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再审中,被申请人宁波中缝公司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8:省高院(2010)浙民申706号民事裁定书,证据9:宁波中院(2010)浙甬商终45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10:北仑法院(2009)甬仑商初字137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1)关于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抽逃出资,通过其在乐清伟业公司作挂帐处理的事实,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2)该部分生效的法律文书,不属于本案的再审范畴。证据11:北仑公安局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经过宁波北仑公安的侦查,也认定张章生作为中缝公司的股东具有抽逃出资的事实。证据12:北仑工商局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宁波工商局北仑分局于2009年6月1日对张章生进行了询问,张章生明确表示强调其注册资本在“帐面上”一直是到位的,只不过有些业务往来款未清。
张章生的质证意见:证据9、10、11、12,这些证据原审中都提交过的,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双方诉讼已有9年,原先的裁定都认定张章生有抽逃出资的嫌疑,并未确认张章生有抽逃出资的事实,且这些生效的裁判文书仅是裁定,是程序性的审查。北仑公安局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抽逃出资的证据,不然公安会提起公诉。证据8、9、10,是程序性的裁定,并未审查实体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证据9、10、11、12,被申请人在原审中均已经作为证据提交,不属于再审新证据,对于证据8,系本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除对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补充查明:(1)2004年9月19日,宁波中缝公司各方股东认可截止2004年9月19日张章生实际到位股金640万元。(2)乐清伟业公司股东张章生、周芝瑛对于“宁波中缝公司2004年1月13日支付至北京市大红门长谊缝纫机修理店的338万元、2004年3月1日支付的100万元,合计438万元系宁波中缝公司支付乐清伟业公司预付货款,乐清伟业公司实际收到该笔款项”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实缴资本制下,股东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为:(1)主体为股东。(2)主观方面为故意。(3)客体。股东抽逃出资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司的合法权益和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4)客观方面,抽逃不同于一般的交易,一般的交易是有公正、合理的对价,但“抽逃”是指股东出资资金或者相应的资产从公司转移给股东时,股东并未向公司支付了公正、合理的对价,即未向公司交付等值的资产或权益。这也是认定抽逃出资行为的关键所在。
本案中,其一,2004年1月5日,经宁波雄镇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张章生实缴13269910元,其认缴的13269526.08元注册资本全部到位。2004年1月6日,宁波中缝公司成立,针对注册资本到位问题,股东内部达成协议,中方股东注册资本可与外方股东注册资本同步到位。2006年12月,外方股东出资全部到位。其二,2004年1月13日,中缝公司通过银行向北京市大红门长谊缝纫机修理店汇款两笔,一笔人民币1260000元,另一笔人民币3380000元;同年3月1日,中缝公司通过银行向长谊缝纫机店汇款人民币1000000元。该店系以张章生为业主的个体工商户,已于2006年5月12日注销;2004年6月6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出具借条两份,分别借款人民币3000000元和人民币2000000元;2004年7月14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出具借条一份,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2004年7月16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借款人民币206600元;同年10月11日,张章生向中缝公司出具借条一份,借款人民币116991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14016510元。此外,张章生于2004年8月16日归还中缝公司人民币2760000元,于同年10月5日归还人民币6600元,于同年12月10日归还人民币6869910元,合计人民币9636510元。张章生借离款项与归还款项差额为人民币4380000元(计算公式:14016510元-9636510元)。其三,张章生认为,该人民币4380000元并不存在,相关财务凭证记载2004年6月8日中缝公司预付货款人民币5680000元,至始至终未出现人民币4380000元这一数字,如认为4380000元以预付货款形式挂账处理,但该款项又在乐清伟业公司的供货过程中不断减少,截至2007年仅剩余人民币743436.31元。虽然双方对于供货的具体数额存有争议,但是,乐清伟业公司与宁波中缝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挂账的预付款在账面上也在乐清伟业公司与宁波中缝公司的实际交易中逐渐减少。且乐清伟业公司的股东(张章生51%、周芝瑛49%)也均予以认可的情况下,张章生向宁波中缝公司借款的行为结合乐清伟业公司向宁波中缝公司供货,并未使公司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不符合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权益受损的客观要件。其四,北仑法院(2009)甬仑商初字第1377号民事裁定、宁波中院(2010)浙甬商终字第457号民事裁定以及本院(2010)浙民申字第706号民事裁定均系程序性的审查,并非认定张章生抽逃出资的实体判决,不具有既判力。
综上,原审认定张章生构成抽逃出资,宁波中缝公司与乐清伟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可另行理直,系法律适用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4年修正)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880号民事判决和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4)甬仑商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各项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68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898元,均由宁波中缝精机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培良
审 判 员 梅 冰
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
嘉兴市××有限公司等诉嘉兴市××置业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浙民二终字第1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甲。
委托代理人:徐××。
委托代理人:吴××。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
委托代理人:吴×。
委托代理人:朱乙。
原审第三人:嘉兴市××区人民政府××办事处。
负责人:沈××。
委托代理人:王××、朱丙。
上诉人嘉兴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嘉兴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都××)、原审第三人嘉兴市××区人民政府××办事处(以下简称新嘉××办事处)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嘉民二初字第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汤玲丽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许江杰、代理审判员余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08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王江水、新都××的委托代理人朱乙、吴×、新嘉××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新都××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提供署期为“2007年2月8日”的协议书一份,协议当事人分别某某方某嘉街道办事处、乙方某都公某、丙方某创公某,协议载明:“由于甲乙双方合作丙方资质升级需要,甲方于2004年4月20日向某方甲往来款人民币500万元用于对丙方增资,丙方在大桥工业园开发建设中与乙方业务往来款人民币98万元、24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838万元,根据甲、乙、丙三方乙后同意,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与乙方甲的往来款838万元人民币,经丙方丙确认由其承担。至此,甲方与乙方、丙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关系。2、甲乙丙三方丙在三方签字后生效,以上三方据此协议,作为财务上帐务处理的依据。3、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自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新嘉××办事处书记高某某、新都××法定代表人胡××、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甲分别在协议书法人代表一栏内签字,新嘉××办事处还加盖了公章。新都××依据该协议书,要求新××公司支付该838万元款项,并主张838万元的具体组成为:2003年5月23日、2004年3月19日,新都××以投资款的名义分别支付给案外人嘉兴市新嘉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某(以下简称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28万元、70万元;2004年5月27日,新都××以借入款方式通过银行支付给新嘉商业公某的500万元;2004年6月8日,桐乡市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下称“桐乡创业”)以借款形式支付给新××公司的240万元。桐乡创业(新都××持股75.5%)于2007年10月31日出具债权转让确认书一份,称其已在2007年2月8日协议书中,将该240万元债权转让给新都××。
新嘉××办事处会计陈某某在2007年12月25日原审法院向其调查时称:“协议书是作为新××公司置换的帐务处理协议,三方为了帐目平衡;协议书中‘2004年4月20日’的500万元即新都××提供的2004年5月27日收据中的500万元,签订协议书的主要目的是新嘉商业公某收取了新都××的500万元,但都给了新××公司(2004年5月31日以投资款名义支付),实际并没有用该笔资金,2007年由于某某商业公某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出面进行了处理,签订协议后,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只是新都××与新××公司之间的关系了,至于500万元给了新××公司后,怎么运作也不清楚;98万元和240万元我们不清楚,只是新都××和新××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过新嘉基础设施公某是新都××和新××公司共同设立的,我们退出了新××公司70%股份后,就取得了新嘉基础设施公某100%的资产,前提是新××公司要承担新嘉基础设施公某2940万元的债务;2940万元的债务与协议书中新××公司要承担的838万元是没有关系的,协议中只有500万元是通过我们中转的,至于此后新××公司如果付给新都××,应该有付款凭证,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新××公司应该付给新都××”。2008年3月14日,陈某某向本院陈述称:协议下方的“2007年2月8日”手写的字是其所写,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就是2007年2月8日,胡××和朱甲签字在先,都在2007年2月8日,高书记签字盖章在后。
原审法院另查某,新××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24日,成立时股东分别为新嘉商业公某(出资300万元,占60%)、新都××(出资150万元,占30%)和嘉兴市新嘉物业管理有限公某(出资50万元,占10%)。新嘉商业公某系新嘉××办事处下属公某,后根据有关文件被撤销,由新嘉××办事处统一设置嘉兴市秀城区新嘉街道经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新嘉发展中心)。2004年6月4日,新××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其中嘉兴市秀城区(现为南湖区)新嘉发展中心出资1350万元(占67.5%),新都××出资600万元(仍占30%),嘉兴市新嘉物业管理有限公某出资50万元,占2.5%。2005年1月31日,新××公司经工商登记核准股东变更为新嘉发展中心(出资1040万元,占52%)和新都××(出资960万元,占48%)。此后,两股东的持股比例又进行了调整。
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前身为新嘉工业园区公某,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原为新××公司(出资72万元,占72%)和新都××(出资28万元,占28%),后注册资本变更为350万元,股东持股比例不变。2005年2月18日,该公某股东经工商登记变更为新嘉发展中心(出资98万元,占28%)和新××公司(出资252万元,占72%)。
原审法院再查某,2005年9月13日,新××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会议纪要,新嘉商业公某(即新嘉发展中心)退出在新××公司的70%股份,并分得提前收益2940万元,同意新嘉商业公某在新××公司70%的股权置换新××公司在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所有股份,在股权置换后,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用于某某工业园开发建设的2940万元债务,由新××公司承担;同时,新都××将其持有的新××公司30%股份转让给朱甲。2005年12月之后,新××公司股东变更为朱甲和汪某某。
2007年11月9日,新都××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7年2月8日,新都××、新××公司与新嘉××办事处签订协议书,约定新都××与新嘉××办事处发生的往来款838万元由新××公司承担,但新××公司一直拒绝履行付款义务,请求判令:1、新××公司立即向新都××支付约定款项838万元;2、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新××公司答辩称:2007年2月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书只签字不盖章,只是作为财务帐目处理的依据,对外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不能作为约定承担往来款838万元的依据,新××公司与新嘉××办事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往来款838万元。根据2005年新嘉街道所属公某改革小组文件及股权置换协议书,新××公司与新嘉××办事处在2005年11月29日后已经对帐清楚,新××公司已承担新嘉基础设施公某2940万元的债务,根本不可能在2007年再对2005年已处理完毕的事宜,再进行债务承担。请求驳回新都××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新嘉××办事处陈述称:新××公司所称的协议书不生效、不成立以及仅作财务处理不能成立,2007年2月8日,三方负责人都在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协商,当天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协议应当是合法有效的,838万元应当由新××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新××公司原系新都××与第三人新嘉××办事处共同投资设立,此后新都××和新嘉××办事处均以不同方式退出新××公司,各方当事人之间基于相互之间的投资及合作关系,长期以来互有频繁的经济往来,并产生多起诉讼。本案中主要围绕署期为“2007年2月8日”的协议书效力、签订过程、签订时间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首先,从协议书的表面形式来看,新都××法定代表人胡××、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丁在协议书“法人代表”栏内签字,新嘉××办事处书记高某某签字并加盖公章,尽管协议书第3条约定“自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但并未将签字和盖章作为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故签字和盖章并非缺一不可,而协议书第2条亦约定三方签字后生效,故该协议书在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已具备生效要件。其次,关于协议书的用途及效力问题,从协议书第1条内容来看,新××公司明确同意由其承担新都××与新嘉××办事处的往来款838万元,虽然协议书第2条同时某某“三方据此协议,作为财务上帐务处理的依据”,但与前述第1条内容并不矛盾,并不当然排斥该协议的法律效力,且新嘉××办事处对于新××公司的上述说法并不认同,因此,新××公司仅以此条款试图否认协议书法律效力的说法缺乏相应的依据,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协议书的订立时间,根据新嘉××办事处会计陈某某的陈述,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在2007年2月8日,高某某书记签字盖章时间在此之后,新都××法定代表人胡××也表示其和朱甲签字的时间为2007年2月8日,新嘉××办事处书记高某某何时签字盖章不清楚,应该是在此之后,双方陈述基本一致,而新××公司在答辩意见中认可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7年2月8日,其法定代表人朱甲在庭审时亦表示协议的签订时间应该是在2007年,只是具体时间记不清楚,通过上述证据及陈述,可以初步确定本案协议书的最终生效时间为2007年2月8日之后,现新××公司提出异议并要求对协议时间进行鉴定,与之前其所作的陈述并不一致,而其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一再主张协议签订时间为2005年至2007年间,以此证明协议并非2007年2月8日签订,但在第三次庭审中亦表示鉴定意义不大,可见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而非签订时间,故对于新××公司这一抗辩及鉴定申请,均不予采信。最后,就协议书中838万元款项的组成,新都××已分别提供了相应的付款凭证,其中500万元系2004年5月27日由新都××以借款的方式支付给新嘉商业公某,98万元系2003年5月、2004年3月新都××分两次支付给新嘉工业园区公某(即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前身)和新嘉基础设施公某,240万元系桐乡创业出借给新嘉基础设施公某,桐乡创业又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新都××,该三笔款项虽然收款人分别为新嘉商业公某和新嘉基础设施公某,但新嘉商业公某作为新嘉××办事处所开设的公某,在签订协议书之时早已不存在,而新嘉××办事处此时系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唯一真正投资人,故上述债务均由新嘉××办事处在协议书中一并处理亦无不当。至于新××公司提出500万元和98万元均系股本金,不得收回的问题,由于在签订协议之时,新嘉××办事处与新××公司、新都××与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已无投资关系,已非两公某股东,故并不存在抽逃股本金的问题,且对于新都××而言,500万元系支付给新嘉商业公某的借款,即便新嘉商业公某此后将该款作为股本金投入新××公司,亦与新都××无关,98万元虽系新都××直接支付给新嘉基础设施公某,但协议书中的偿还主体为新××公司,并非新嘉基础公某,因此,同样不存在抽逃注册资本之说。此外,桐乡创业虽曾向新××公司借款450万元,并经原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但已履行完毕,因此桐乡创业将240万元债权转让给新都××,并由新都××在协议书中一并处理,并未损害新××公司的权益。综上所述,新都××、新××公司及新嘉××办事处签订的三方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新××公司自愿承担新都××与新嘉××办事处关联企业所发生的838万元往来款,其应严格予以履行,支某某都公某该笔款项,至于新××公司在承担该笔债务后,如认为其与新嘉××办事处之间因股权置换等尚有其他经济纠纷,可另行解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华某某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某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于2008年5月4日判决: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某某都公某人民币838万元。如新××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460元,由新××公司负担。
宣判后,新××公司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判认定基本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协议书尚未生效。协议第3条约定“自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故签字和盖章为协议生效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原判认定协议已经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名而生效错误。2.即使协议书真实有效,本案协议书履行期限不明,根据合同法规定,须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判直接支持新都××的诉讼请求错误。3.签订本案协议书的真实目的并非确定债务,而只是提供财务处理依据。新都××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于2004年5月27日向案外人新嘉商业公某支付500万元(借款)、于2004年3月19日、5月23日分别向新嘉基础设施公某支付70万元和28万元,以及案外人桐乡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于2004年6月8日向案外人新嘉基础设施公某支付240万元。无论支付时间还是支付对象都与协议书所描述的过程大相径庭,足以证明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协议书上签名位置在协议上部当事人状况栏,并未按照正常的署名盖章格式,且协议书原件3份均在原审第三人处,新都××法定代表人庭审中承认是在2007年6月份去第三人那拿的,更加说明该协议书系帐务处理用。4.协议书所涉的案外人对新××公司不享有债权,如按原判认定将只做帐务处理依据的协议书变成实实在在的债务,根本无法解释新××公司在毫无对价的情况下承担如此巨额债务的合理性。二、原判将新都××向案外人付款的行为认定为协议书中的三方款项往来,并认定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审第三人无权为新嘉商业公某及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处理债务。新嘉商业公某在签订协议时已不存在,并办理注销手续。按常理,在债权债务没有清理或有人承担之前,工商部门不会办理相关手续。在毫无证据情况下,原判直接认定新嘉商业公某债权债务由原审第三人处理,显然没有依据;而新嘉基础设施公某依然存在,其接受新都××的98万元只能由它自己出面处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原审第三人得到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事前授权或事后追认,故第三人根本无权处理案外人之债务。2.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让新××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桐乡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将其享有的对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债权,原判判令由新××公司向新都××承担,有违合同法中对于债权债务转让的规定,一方面该债权转让未履行通知义务;另一方面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并未将债务全部转让给新××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新××公司根本不是履行义务人,不存在法定的履行义务;况且原审第三人未得到新嘉设施公某授权或追认的情况下,擅自在协议书中处理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债务行为系无权处分行为,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某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新都××的诉讼请求。
新都××答辩称:一、原判关于三方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认定正确。该协议书形式符合约定和法定的生效条件,“签字盖章”不同于“签字并盖章”,各方法定代表人已签字,故协议生效。对履行不明的债权,债权人不经催告程序可以直接起诉。协议兼具“债权凭证”与“帐务处理”性质,约定内容应该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况且,新××公司、新都××原先是原审第三人的下属企业,在改制前,新××公司、新都××与原审第三人下属的其他企业都互有参股及资金往来,新××公司承担该838万元债务有明确对价,退一步将,即使没有付出对价的债权人取得债权,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二、原判判令新××公司支某某都公某838万元完全正确。因本案所涉的新嘉商业公某、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均为原审第三人下属公某,原审第三人有权处理下属企业的债权债务;桐乡创业公某将其对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债权转让给新都××,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又将债务转让给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将该债务置换给新××公司,因此新都××有权向新××公司主张。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嘉××办事处答辩称:本案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判事实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新都××、新嘉××办事处均无新的证据提供。
新××公司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新嘉商业公某的法人证书,证明该单位至今客观存在,尚未办理注销手续;2.嘉兴市秀洲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法人证书,说明其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系事业单位的独立法人;3.企业法人的年鉴报告书,证明新嘉基础设施公某至今法人资格存在,股东为嘉兴市秀洲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和嘉兴市新嘉资产经营中心;4.新嘉××办事处的证明一份,载明新嘉商业公某已变更为嘉兴市南湖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证明嘉兴市××区人民政府××办事处出具不实证明。
新都××质证认为,原审时其已经提供了新嘉商业公某被撤销变更的证明,故新××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一不足以对抗新都××的证据。证据材料二可以看出该公某开办单位是新嘉××办事处,具体由该办事处质证,但恰好可证明新都××的主张,即新嘉××办事处系嘉兴市秀洲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开办单位。证据材料三与本案所涉838万元没有因果关系。证据材料四是新嘉××办事处开具的证明,新都××无法质证。证据材料一、材料四只能证明企业开业情况,无法证明现在是否还存在的事实。总之,新××公司提供的四份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目的。
新嘉××办事处质证认为,新嘉商业公某已注销是事实,目前已无机构、地址和人员,手续是否办理须核实。对证据材料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商业公某类似于商业管理办公室的性质,后因事业单位改革,其职能转化给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所以街道办事处出具此证明,并非如创业公某所言属企业承继关系。
本院认为,证据材料一反映新嘉商业公某尚未注销的事实,新嘉××办事处对此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在庭后也没有提供新嘉商业公某已办理注销手续的证明,故该证据材料可作为二审证据使用;证据材料二能证明嘉兴市秀洲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企业性质及开办单位,新都××对此亦无异议,可以作为二审证据使用;证据材料三证明的是新嘉基础设施公某于2006年3月的年鉴材料,新嘉××办事处对此亦无异议,可作为二审证据使用,但该材料只能反映2006年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存续情况,无法证明目前该企业是否注销。证据材料四欲证明的是街道办事处出具不实证明,与本案纠纷无关联性,不予采纳。
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签署时间为2007年2月8日的协议是否生效问题。1.从协议形式要件看,新都××法定代表人胡××、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丁在协议书“法人代表”栏内签字,新嘉××办事处书记高某某签字并加盖公章,符合我国合同法关于协议生效形式要件的规定;2.从一般常理可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书上签名,应当是基于对协议记载内容的全部认可,否则,其应当作相反的或限制性的说明;因此,三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3.协议不仅约定了“签字生效”,还约定了“自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两者似存在冲突。但“自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条款的约定,词意上并没有将盖章签字作为必须同时具备的生效条件,且根据司法实践,在法定代表人已经签字的情况下,即使约定“盖章并签字”生效的协议,亦应认定已经生效;4.该协议书涉及的内容是新××公司对街道办事处与新都××往来款以及新××公司与新都××往来款838万元负担的确认,此种债务承担或代为履行的承诺一般只要三方合意,即发生法律效力,故内容上亦无违法之处。据此,应认定本案协议已经生效。
二、对本案协议书中“作为财务上帐务处理的依据”的文意理解问题。首先,在承担838万元债务的协议上签名,对任何人而言绝非儿戏,朱甲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三份相同而非一份协议书上分别签字,诉讼中再以只作“帐务处理”论理,实难自圆其说。其次,如果协议确为办事处帐务应付所用,依正常的处理习惯,在完成该“阳”协议同时,一般会对协议签订情况进行说明而签订“阴”协议,以保护自己的权益,遏制假债务真承担结果的发生。而本案除承担债务的协议外,再无其他书面材料反证。第三,“财务上帐务处理的依据”的说法,较为含糊笼统,因债权凭证本属财务上帐务处理的依据,从词义上难以得出协议虚假的结论。
三、关于本案协议所涉款项流转是否合法问题。我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也就是说,债务转移经债权人同意即能生效。本案协议中涉及598万元的债务转移,新××公司承诺承担,债权人新都××予以同意,形式要件上符合合同法规定,为有效的债务转移。协议约定的240万元债务转移内容,为案外人桐乡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向新嘉基础设施公某支付,在原审时,桐乡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新都××控股)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债权转让确认书”,同意债权转让给新都××,认同债务由新××公司承担的协议内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桐乡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转让给新都××之债权,新都××已经接受。就书面材料看,确没有反映桐乡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某曾通知新嘉基础设施公某债权转让的事实。但是,本案涉及的新嘉××办事处、新都××、新××公司、新嘉商业公某、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等均属于关联性企业,协作时间长,往来款项多,而新嘉××办事处为新嘉商业公某、新嘉基础设施公某的开办者,担任了对新嘉商业公某、新嘉基础设施公某资产置换与处理的职责,其已在2007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中认可了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的事实。因此,2月8日协议所涉款项的流转,形式上虽存瑕疵,但契合当事人间相互交错的关联实情,也没有违法或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故该协议所涉几笔款项的流转无不当之处。
综上,新都××提交的证明其与新××公司间债权债务关系的2月8日协议,从其文意记载反映了新××公司负有支某某都公某838万元款项的内容。新××公司如认为该协议书不真实或债权债务不成立,其须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从一、二审情况看,新××公司提供的反驳证据并不充分,综合本案当事人举证情况,新都××提供的协议书等证据的证明力大于新××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中,原审法院已经注意到了几方关联主体间的特殊关系和利益平衡问题,如新××公司与新嘉××办事处间存在股权置换等其他纠纷,可以另行解决。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460元,由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玲丽
审 判 员 许江杰
代理审判员 余 音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浙商初字第5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负责人:张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卢燎峰、张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世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芳,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虞松涛,上海天尚(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赛飞,该公司总裁。
委托代理人:章晨煜,该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李宝枢,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鑫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明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迪,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皇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丽芳,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晓军,上海天尚(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诉被告杭州世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世茂公司)、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世茂公司)、江苏鑫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江苏皇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合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范启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丽、代理审判员余之悠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1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卢燎峰、张熙,被告杭州世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虞松涛,上海世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章晨煜、李宝枢,鑫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迪,皇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晓军到庭参加诉讼。后合议庭成员余之悠因故调整为审判员孙光洁,本案于2016年2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卢燎峰、张熙,被告上海世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章晨煜、李宝枢,鑫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曹迪,皇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晓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杭州世茂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诉称:一、截止2015年5月31日,借款人杭州世茂公司仍有借款本金38000万元及利息6412557.31元,罚息3714155.32元、复利108.67元未能清偿;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杭房建经字第15002743号】它项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依法享有优先权;上海世茂公司对杭州世茂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1年4月,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浦东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杭州世茂公司达成一致,由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中国银行浦东支行组成银团贷款为上海世茂公司的子公司杭州世茂公司提供8亿元的授信。为此各方签订了下列合同:2011年4月,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中国银行浦东支行签订了《内部银团贷款协议》,双方就贷款份额、贷款管理、出现不良时的清收等作出约定和安排。
2011年4月22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11NRJ017)一份,约定:杭州世茂公司因开发杭州下沙世茂广场项目建设需要向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借款,借款金额为8亿元整,借款期限为48个月,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三年以上至五年(含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逾期罚息为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40%。杭州世茂公司同时承诺:如发生股权转让、重大资产转让和债权转让以及其他可能对其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时,须事先征得杭州世茂公司的书面同意。2011年4月22日,杭州世茂公司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编号11NRD002),约定杭州世茂公司以其名下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14号路以南,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1年4月26日办理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杭土抵他项2011第043号】。2015年2月4日,又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编号11NRD003),约定以其名下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的在建工程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5年2月10日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杭房建经字第15002743号】。2011年4月22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编号11NRB023号)一份,约定由上海世茂公司为杭州世茂公司在《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上海世茂公司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进行抗辩。上海世茂公司同时承诺:在杭州世茂公司还清贷款前,不减少和撤回其作为股东对该项目的投入,不进行股东利润分配。借款合同签订后,根据杭州世茂公司的申请,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于2011年陆续发放了合计金额6.7亿元的贷款。但杭州世茂公司未能依约按期向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还本付息。
二、上海世茂公司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鑫源公司、皇合公司明知上海世茂公司抽逃出资,低价受让杭州世茂公司股份。1)杭州世茂公司于2010年注册成立,至2010年11月16日其注册资金为8.4亿元,全部由上海世茂公司出资,法定代表人为许薇薇,2013年6月上海世茂公司将其中90%的股权转让给了鑫源公司。牡丹江茂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茂源")注册地黑龙江绥芬河,注册资本2000万元,系上海世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上海世茂公司在担任控股股东期间,利用其对杭州世茂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通过虚构贸易等方式将杭州世茂公司巨额资金通过上海世茂公司控制的其它公司如牡丹江茂源等关联公司转至上海世茂公司。经调查,2010年至2013年间杭州世茂公司仅通过牡丹江茂源流向上海世茂公司的资金即达9.9亿元。杭州世茂公司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向牡丹江茂源累计流出资金约9.9亿元。其中:(1)杭州世茂公司2010年度审计报告(浙中信2011审字第86号)附注第18页:预付账款,杭州世茂公司支付给牡丹江茂源的预付账款为2亿元;(2)账号为35×××98的贷款账户流水:自2011年5月4日至2012年1月4日间,杭州世茂公司贷款资金受托支付至牡丹江茂源共计3.8650亿元;(3)账号为38×××71的企业账户流水:自2011年1月19日至2012年11月15日间,杭州世茂公司仅大额资金流入牡丹江茂源共计约3.5亿元。(4)账号为37×××78的企业账户流水:××年4月6日和2011年5月20日,杭州世茂公司仅大额资金流入牡丹江茂源共计约0.53亿元。上述款项合计约9.9亿元。牡丹江茂源作为上海世茂公司的资金平台流入流出资金规模较大,根据账号为44×××71的企业账户流水显示,2010年8月至2013年底间,牡丹江茂源通过该中国银行账户向上海世茂公司净流出资金约66亿余元。杭州世茂公司大额资金流入牡丹江茂源后,几天后即流向上海世茂公司。杭州世茂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流入牡丹江茂源2亿元,1月21日即全部流向上海世茂公司;5月4日和5月12日杭州世茂公司贷款资金受托支付至牡丹江茂源1.8亿元,5月19日牡丹江茂源流入上海世茂公司2.6亿元;6月23日杭州世茂公司贷款资金支付至牡丹江茂源0.6亿元,6月30日牡丹江茂源流入上海世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世贸影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0.6亿元;10月28日杭州世茂公司流入牡丹江茂源0.6亿元,10月31日从牡丹江茂源划转0.6亿元至上海世茂公司。杭州世茂公司资产严重缩水。杭州世茂公司的资产价值应不少于其注册资金和银行贷款之和,即12.2亿(84000万注册资金+38000万贷款余额)。而根据杭州世茂公司2015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资产总计仅仅为6.47亿元,资产缩水明显,显然是抽逃出资的后果。2013年6月,上海世茂公司将杭州世茂公司股权的90%转让给鑫源公司,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办理了杭州世茂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2014年11月18日,鑫源公司又将其持有的杭州世茂公司90%股权转让给皇合公司,双方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鑫源公司和皇合公司明知前手股权存在瑕疵仍然受让了瑕疵股权。由于项目公司的资金被抽走,造成项目公司资金链断裂,施工单位撤出,项目停工,楼盘烂尾。上海世茂公司、杭州世茂公司、鑫源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资本确定、维持、不变三原则,损害了公司的清偿债务的能力,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上海世茂公司应当对杭州世茂公司的债务承担出资范围内的补偿清偿责任,鑫源公司、皇合公司应当对上海世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请求判令:一、杭州世茂公司作为借款人逾期未能归还贷款,应就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等承担偿还责任,上海世茂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有权就抵押物行使优先权;上海世茂公司、鑫源公司、皇合公司对抽逃公司出资负有法律责任,杭州世茂公司立即偿还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380000000元、利息6412557.31元,罚息3714155.32元、复利108.67元(利息和罚息计算至2015年5月31日),合计390126821.3元,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至实际清偿日的全部利息和罚息;二、杭州世茂公司支付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494万元;三、确认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杭州世茂公司名下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14号路以南,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上在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就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上海世茂公司不以抵押物的处置为条件对杭州世茂公司的全部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抽逃出资6.86亿元的范围内对杭州世茂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鑫源公司、皇合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的抽逃出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六、本案全部诉讼、保全费用由杭州世茂公司、上海世茂公司、鑫源公司、皇合公司承担。
被告杭州世茂公司答辩称:一、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陈述的事实经过及案件的发生过程和主张的主债务没有异议,但对其主张的律师费存在异议,因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未能提供相应的票据及付款凭证,应以实际产生的律师费用为准。二、结合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间签订的《保证合同》及其提供的资金流动明细来看,上海世茂公司应就主合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海世茂公司在其实际控股期间提供牡丹江茂源抽回资金的行为,杭州世茂公司作为上海世茂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对于整个案件的发生全无控制权,也无法阻止。综上,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主张的主债务本公司予以认可。上海世茂公司作为知名上市房地产企业,除通过经营获取利润之外,更应依法合规经营并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现上海世茂公司利用其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抽回资金的行为,不仅造成本公司的偿还能力严重下降,使得工程项目无以为继,也违反了二者之间的《保证合同》,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告上海世茂公司答辩称:我公司要求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明确诉讼请求,即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合同依据及要求判决我公司抽逃资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上海世茂公司的保证责任范围及承担问题。上海世茂公司认为担保责任对应的主债务为2.1亿元,该债务已得到清偿,故上海世茂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主要理由:1、《借款合同》第九条第1款明确约定上海世茂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务范围是抵押担保以外的部分即4.6亿元抵押贷款以外的3.4亿元而非被答辩人主张的全部债务;2、基于《借款合同》第五条第9款约定先放抵押担保项项下贷款4.6亿、被答辩人第8项证据表明本案实际借款为6.7亿、被答辩人2013年3月函,上海世茂公司担保的主债务范围实际为2.1亿元;3、上海世茂公司第4项证据及被答辩人证据9表明杭州世茂公司已偿还贷款2.9亿,该还款“对应"并“覆盖"了上海世茂公司担保项下的主债务2.1亿元。二、关于6.86亿元债权转移是否构成股东抽逃出资的问题。上海世茂公司认为被答辩人诉称上海世茂公司至少抽逃注册资本6.86亿并要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主要理由:1、上海世茂公司证据9及被答辩人证据10表明上海世茂公司注册资本8.4亿已完全到位;2、上海世茂公司证据10表明杭州世茂公司仅支付土地出让金等款项就达人民币6.2亿元,不存在至少抽逃6.86亿注册资本的可能性;3、上海世茂公司与杭州世茂公司间债权债务公开且真实,上海世茂公司因股权转让产生的6.86亿元债权抵销应付债务,杭州世茂公司因此对鑫源公司享有的6.86亿元债权,该处置合法、有效,且该债权债务处置与注册资本无关。综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关于要求上海世茂公司对杭州世茂公司全部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鑫源公司答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规定,对于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现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上海世茂公司实施抽逃出资的行为要求其承担责任,从诉称的事实看,在上海世茂公司实施抽逃出资期间,鑫源公司既不是杭州世茂公司的股东,也未参与经营管理,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抽逃出资承担责任的主体。故无论上海世茂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并承担责任,均与鑫源公司无关。二、鑫源公司与上海世茂公司仅是股权转让关系,且鑫源公司已将上海世茂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对于上海世茂公司被诉的抽逃出资,鑫源公司并不知情,也没参与和受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要求鑫源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的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请求驳回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的诉请,我方保留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错误保全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
被告皇合公司答辩称:首先,对于案涉《金融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均无异议,故对案涉主债权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均无异议。其次,上海世茂公司应当就合同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照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一、二条约定,上海世茂公司应就编号11NRJ017《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承担全部连带保证责任;第四条约定,主债务在保证合同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在该保证合同项下任何权利的行使,且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第八条第7项还约定,保证人承诺在还清贷款前不偿还股东借款和支付利息,不减少和撤回股东对该项目的投入,不进行股东利润分配。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资金流动明细来看,杭州世茂公司在上海世茂公司的实际控制期间,有大量的资金流入同样是上海世茂公司全资控股的牡丹江茂源,同时牡丹江茂源又有大量的资金回流至上海世茂公司的账户,并在牡丹江茂源账上形成了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巨量应收账款。虽然上海世茂公司在庭审时辩称杭州世茂公司与牡丹江茂源之间的资金往来及牡丹江茂源与上海世茂公司的资金往来关系与本案所涉金融借款合同无关,但结合上海世茂公司提供的第12号证据即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第2款下第(4)项的约定来看,可以确定在二者进行股权转让时,上海世茂公司实际已经确认对杭州世茂公司负有6.86亿元债务。上海世茂公司作为杭州世茂公司的全资控股股东,与杭州世茂公司间并无直接关联交易,且已经出资到位,故结合相关的资金流动情况,可以得出上海世茂公司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抽回经营资金的行为,无论该抽回资金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上海世茂公司均已违反《保证合同》约定的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上海世茂公司应就杭州世茂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三、上海世茂公司抽回资金的行为均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并无双方恶意串通、试图逃避债务的证明。且皇合公司系从鑫源公司处通过股权转让获得杭州世茂公司的股权,此前不可能知道上海世茂公司控制期间对杭州世茂公司是如何经营的,皇合公司未实施任何损害杭州世茂公司的行为。上海世茂公司抽回资金的行为违反了保证合同的约定,客观上造成杭州世茂公司偿债能力严重下降,使得工程项目无以为继,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皇合公司并无单独或同其他人实施损害杭州世茂公司利益的行为,故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皇合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诉请。
在举证期限内,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向本院提交了八组共32份证据材料,分别是:第一组:1、《内部银团贷款协议》及其补充协议1份,证明本次贷款发放由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以及中国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共同组成内部银团。2、《固定资产借款合同》1份,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公司于2011年4月22日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相关约定。3、《保证合同》(11NRB023号)1份,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于2011年4月22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就上海世茂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人保、物保的顺序等作出约定。4、抵押合同(11NRD002号)1份。5、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杭土抵他2011第043号)1份。以上4-5号证据共同证明2011年4月22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杭州世茂公司以其名下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14号路以南,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1年4月26日办理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杭土抵他项2011第043号】。6、《抵押合同》(11NRD003号)1份。7、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杭房建经字第15002734号)1份。以上6-7号证据共同证明2015年2月4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追加其名下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的在建工程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5年2月10日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杭房建经字第15002743号】。8、借款借据12份,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于2011年分批向杭州世茂公司发放贷款合计67000万元。9、杭州世茂公司贷款明细、欠息清单6份,证明该公司逾期本息的具体情况。第二组:10、杭州世茂公司工商登记基本信息1份,证明杭州世茂公司原系上海世茂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84000万元。11、牡丹江茂源工商登记基本信息1份,证明牡丹江茂源系上海世茂公司全资子公司。第三组:12、杭州世茂公司资金流水汇总表1份。13、2010年杭州世茂公司审计报告1份。14、杭州世茂公司资金流水明细1份。以上12-14号证据共同证明杭州世茂公司向牡丹江茂源累计流出资金约9.9亿元;15、牡丹江茂源银行流水汇总表1份,16、牡丹江茂源流水明细1份,17、牡丹江茂源2011年度审计报告1份,18、牡丹江茂源2013年度审计报告1份,以上15-18号证据共同证明牡丹江茂源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向上海世茂公司净流出资金约67亿余元。19、牡丹江茂源与杭州世茂公司大额资金流入、流出明细及凭证(节选)1份,证明杭州世茂公司的资金于2011年1月19日、2011年5月4日、2011年6月23日、2011年10月28日分别流向牡丹江茂源合计5亿元后,短时间内又从牡丹江茂源流向了上海世茂公司,其实质为抽逃出资。以上12-19号证据同时共同证明上海世茂公司在担任控股股东期间,利用其对杭州世茂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通过虚构贸易等方式将杭州世茂公司十余亿元的资金通过上海世茂公司的其他全资子公司如牡丹江茂源等关联公司转走,并最终转至上海世茂公司,表面上形成了杭州世茂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巨额债务,实质系将其对杭州世茂公司的出资抽回。20、杭州世茂公司2015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1份,证明杭州世茂公司的资产缩水严重,抽逃出资现象明显。第四组:21、尽职调查报告(正文部分)。22、尽职调查报告(附件部分)。以上21、22号证据共同证明上海世茂公司的抽逃出资的具体情形。第五组:23、委托代理合同、发票、打款凭证各1份,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第六组:24、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关于杭州世茂公司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1份,25、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关于杭州世茂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局备案版本)1份,26、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关于杭州世茂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皇合公司提供版本)1份,以上24-26号证据共同证明上海世茂公司、鑫源公司之间曾签署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在双方隐瞒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私下签订并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各方均约定将上海世茂公司对杭州世茂公司的68600万元债务与鑫源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抵销。第七组:27、杭州世茂公司银行存款三栏式明细账(2011年)1份,28、杭州世茂公司预付账款三栏式明细账(2011年、2013年)1份,29、杭州世茂公司内部往来三栏式明细账(2013年)1份,30、杭州世茂公司其他应付款三栏式明细账(2013年)1份,以上27-30号证据共同证明:1、上海世茂公司在担任杭州世茂公司全资股东期间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情况以及杭州世茂公司向上海世茂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世浦、牡丹江茂源)预付款项的情况;2、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在进行股权转让前后,686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未发生实际的资金交付,而是通过债权债务转让、股权转让,相互抵销的方式进行账务处理。第八组:31、上海世茂公司2012年审计报告1份,32、鑫源公司2012年审计报告1份,以上31-32号证据共同证明第一次股权转让前,上海世茂公司净资产远远高于鑫源公司,上海世茂公司的清偿能力远远强于鑫源公司。
被告上海世茂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二组共15份证据材料,分别是:第一组,1、编号为11NRJ017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一份,欲证明上海世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3.4亿元;2、编号为11NRB023的《保证合同》,欲证明上海世茂公司为主合同提供保证;3、证明二份,欲证明黄悦曾任上海世茂公司融资部助理总监,其持有编号为SHGFC0112037工作电脑;4、(2015)沪长证字第6770、6771号公证书二份,欲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2013年4月1日发函要求先行归还案涉贷款余额中的2.7亿元(含担保项下的2.1亿元),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2013年5月24日发函同意上海世茂公司股转请求。上述四份证据材料皆来源于上海世茂公司。5、杭州世茂公司贷款明细表及附件,欲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向杭州世茂公司发放了人民币6.7元贷款,保证担保项下贷款2.1亿元已经根据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要求全额清偿完毕,该证据材料来源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9;6、7是来源于杭州世茂公司的贷款还款凭证和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欲证明杭州世茂公司于2013年5月24日归还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1.7亿元及利息1553066.67元,于2013年5月27日归还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1.2亿元及利息1725281.89元。上述七份证据材料可以证明杭州世茂公司已经提前归还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人民币2.9亿元包括上海世茂公司担保项下的贷款2.1亿元。第二组包括八份证据材料,8、9是来源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的公司基本情况和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及聚信会验(2010)第3号验资报告,欲证明杭州世茂公司的股东为上海世茂公司(占股10%)及皇合公司(占股90%),上海世茂公司对杭州世茂公司充分履行了人民币8.4亿元的出资义务;1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二份、缴款书、税收通用缴款书,欲证明杭州世茂公司实际支付土地款601210000元及契税18036300元,来源于杭州世茂公司;11、情况说明,欲证明杭州世茂公司划转至牡丹江茂源款项及用途,来源于牡丹江茂源;12、股权转让协议书,欲证明鑫源公司以7.56亿元向上海世茂公司受让杭州世茂公司90%股权,7.56亿元转让对价分为7000万元现金及6.86亿元债务,来源于上海世茂公司;13、关于杭州世茂公司股东变更的同意函,欲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已经书面同意鑫源公司受让杭州世茂公司90%的股份,来源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14、杭珠会审(2014)第144号杭州世茂公司审计报告,欲证明股权转让完成后,杭州世茂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享有37951556.13元应收款,对鑫源公司享有6.86亿元应收款,来源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15、银行结算凭证,欲证明上海世茂公司对杭州世茂公司所有应付款均已履行且超额履行完毕,目前杭州世茂公司应付上海世茂公司15888443.87元,来源于上海世茂公司。上述八份证据材料可证明上海世茂公司已经向杭州世茂公司充分履行了出资义务,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
被告皇合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二份证据材料,分别是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杭州世茂公司于2013年5月22日和2013年6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各一份,欲证明上海世茂公司与鑫源公司就杭州世茂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价款及付款细节的确认,股权转让款中已经扣除上海世茂公司调走的资金。
被告杭州世茂公司、鑫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杭州世茂公司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材料15至19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对证据材料20-22均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3以及证据材料第6至8组均予以认可。对上海世茂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至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材料6至10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材料11至12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材料13至14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材料1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杭州世茂公司对皇合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的三性无异议。
上海世茂公司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具体为:对证据材料1,第1份协议原件版本和证据版本不一致,原件版本没有日期,证据版本有日期,其他形式上无异议,第2份协议形式上无异议。两份协议都是银行内部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材料2,原件第6页与证据第6页不一样,主要是8.3,原件上无工作日,对提前还款没有要求,8.4条款,证据上手填了帐号,原件上没有帐号。跟原来我们拿到的借款合同的复印件也有差异,我们拿到的放款帐户和还款帐户是同一个,现在提交的放款帐户和还款帐户不是同一个。对合同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4—7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15年2月新的抵押合同,在2.9亿清偿后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的抵押合同,价值8.2亿和3亿,以4.6亿担保债权,担保债权3.8亿,担保价值远远超过主债务的价值。对证据材料8形式真实性无异议,系主债务人和出借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借款金额应该由杭州世茂公司进行确认。对证据材料9,真实性无异议。与上海世茂公司计算的利息略有差异,但差异不大。对证据材料10—11,无异议。对证据材料12—14,系杭州世茂公司和牡丹江茂源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系,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材料15—19,牡丹江茂源的财务材料,与本案也没有直接关系,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材料20,来自于原告和杭州世茂公司委托的调查报告,上海世茂公司没有参与,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资产负债表只有杭州世茂公司的公章,但负责人、财务经理等等都没有相关签名,不符合资产负债表的要求。第555页的资产负债表和报告里面的资产负债表也是不一样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21—22,即由原告和杭州世茂公司作的报告。报告第10页即证据566页,对本案争议的3.8亿作了明确的表述,就是抵押项下的、本案争议的3.8亿与上海世茂公司的保证责任没有关联性。对证据材料23,委托合同、发票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打款凭证不予确认,因为原告就是中国银行,凭证上没有银行转契章,并不能证明已经完成了转帐。对证据材料24—26,三份转让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同意,不存在隐瞒的问题。对证据材料27—30,杭州世茂公司的银行明细,暂时无法确认真实性。对证据材料3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材料32,不是当事人,无法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上海世茂公司对皇合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其来源不合法,无法发表质证意见。
鑫源公司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9,本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不清楚,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10—11,真实性无异议,没有关联性;对证据材料12—23,没有关联性,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材料24—26,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材料27—3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材料32,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上海世茂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鑫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11、13-15,不是合同及相对方的当事人,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材料12,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皇合公司提交的二组证据材料鑫源公司质证认为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皇合公司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第一至八组证据材料的三性均予认可。对上海世茂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与杭州世茂公司相同。
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上海世茂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即《固定借款合同》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合同系本行与杭州世茂公司签订,上海世茂公司并不是该份合同的签约当事人,因此不能以该份合同内容确定上海世茂公司的担保范围,而应该以上海世茂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确定其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及范围。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仅仅是贷款发放的前后顺序,而非担保责任的前后顺序,保证责任的承担应以担保合同为准。对证据材料2即《保证合同》的三性无异议。该份合同第二条也恰恰能够证明上海世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债务是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而并非仅承担3.4亿元。合同第八条第7点明确约定,保证人承诺,在贷款清偿完毕前,不减少和撤回对项目的投入。对证据材料3即情况说明(关于黄悦的身份、公证的电脑系上海世茂公司配发)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无法证明黄悦的身份及该笔记本电脑的权属。对证据材料4即公证书1(关于经开支行沈张恒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向黄悦发送函件“建议上海世茂先行归还其担保项下的2.1亿元的贷款“):对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中“安排建议函"的真实性有异议:(1)该公证书公证的过程是对某台电脑里所保存的文件进行打开的过程,而不是对公开网络上电子邮件打开过程进行的公证,无法证明该文件是由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向上海世茂公司发送的,不具有证明力;(2)上海世茂公司并未出示该份“安排建议函"的原件,说明本行并未向上海世茂公司正式出具过这份函件;(3)从该份建议函的内容上看,仅仅是一个安排建议,并不具有变更原保证合同条款的合同效力,不能据此证明本行与上海世茂公司就担保的主债权金额进行了变更约定。而且该份函件中也明确表示基于杭州世茂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股权变更,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需上报风险管理部门报批,结果以报批为准,说明无论是否对原贷款条件担保条件进行变更,都需以上级部门的批准结果为准。公证书2(关于杭州世茂的股权变更同意函):对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该公证书公证的过程是对某台电脑里所保存的文件进行打开的过程,而不是对公开网络上电子邮件打开过程进行的公证,无法证明该文件是由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向上海世茂公司发送的,不具有证明力;(2)从该份同意函的内容上看,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是基于上海世茂公司向本行提供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本行提供的证据24)出具的,而该份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的转让对价与上海世茂公司后来真实履行的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及债务抵销等条款有本质性的差异,因此不能据此证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同意上海世茂公司的股权转让请求,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条件与报批的股权转让条件严重不一致。对证据材料5即贷款明细表及附件: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保证担保项下仅有2.1亿元且已全额履行完毕。对证据材料6、7即贷款还款凭证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仅能证明杭州世茂公司的还款情况,但是不能证明所还款项系归还保证担保项下的债务。对证据材料8即公司基本情况、股东变更情况报告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9即《验资报告》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补充,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杭州世茂公司最初8.4亿元的注册资本是充足的,但是在上海世茂公司全资控股期间,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虚假的基础贸易进行关联交易,不断向关联公司输出资本,导致杭州世茂公司的资产巨额缩水,偿债能力严重下降,并最终通过股权转让的交易安排实现抽逃出资的目的。对证据材料10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款书、税收通用缴款书的三性无异议。恰恰可以印证上海世茂公司是通过注资、拿地、抵押贷款、关联交易、输出资本、股权转让等等一系列的交易安排最终实现将出资抽回的目的。对证据材料11即情况说明(牡丹江茂源出具):证据形式、真实性均有异议。1、该份证据系是牡丹江茂源于2015年9月22日出具,系事后制作,证据形式应该属于单位证人证言,而非书证。既然是证人证言,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则55条的规定,应当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庭接受质证;2、牡丹江茂源系上海世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受上海世茂公司控制,且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人证言采信力极低;3、从该份说明的内容上看,反而印证了在杭州世茂公司净流向牡丹江茂源的9.9亿余元中,真实的工程款贸易往来仅仅只有7900余万元,对其余巨额的资金流出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印证了本质上其就是上海世茂公司抽逃出资的平台。4、该份证据也能印证牡丹江茂源系受上海世茂公司控制。对证据材料12即《股权转让协议书》(债务抵销版本,同原告证据21):三性无异议。上海世茂公司从未向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过该份协议,从该协议内容上看,上海世茂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其担任全资股东期间对杭州世茂公司的6.86亿元的负债与股权受让方鑫源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相抵销,鑫源公司仅仅只支付了7000万元对价款,就取得了注册资本8.4亿元的杭州世茂公司90%的股权,其中该份协议第18页也明确约定:关于6.86亿元股权转让款与杭州世茂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债权相抵消事宜及账务操作给鑫源公司造成损失的,任由上海世茂公司无条件承担赔偿责任。这说明上海世茂公司和鑫源公司当时在签订这份协议时,对于这种变相的抽逃出资的做法本身就达成了一致的默契,并对后续可能产生风险的责任承担作出了约定。对证据材料13即《关于杭州世茂世纪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变更的同意函》:该份证据无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材料14即《杭州世茂2013年度审计报告》(原告证据22):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可以印证上海世茂公司通过债务相抵的形式实现抽逃出资所做的财务账目上的安排和处理。对证据材料15即《银行结算凭证》的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明上海世茂公司转让股权以前,仅仅只向杭州世茂公司流入5300余万元,杭州世茂公司却通过牡丹江茂源向上海世茂公司流入9.9亿余元,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的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上海世茂公司已将杭州世茂公司的出资抽回。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皇合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该二份协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合法性不予确认,是上海世茂公司和鑫源公司为了掩盖其抽逃出资的形式。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1-11,因各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已经发生的金融借款亦有关联,故可以作为认定《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内容及款项往来的依据;对证据材料12-32,因各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均未表异议,可予确认,但对其关联性、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对被告上海世茂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1-2、5-10因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对证据材料3-4、11-15,各方当事人对其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予确认,但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对被告皇合公司提交的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各方当事人对其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可予确认,但对其证明力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2011年4月22日、12月29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作为主办行与中国银行浦东支行作为参加行签订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银团贷款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由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中国银行浦东支行组成银团为杭州世茂公司提供贷款授信,贷款标的为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于2011年4月22日与杭州世茂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11NRJ017)中规定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金额为人民币捌亿元。双方还就贷款份额、贷款管理、出现不良贷款时的清收等作出约定。并明确,如遇原借款合同有关诉讼,由主办行负责诉讼执行等相关事宜。
2011年4月22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公司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11NRJ017)一份,约定:杭州世茂公司因开发杭州下沙世茂广场项目建设需要向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借款,借款金额为8亿元整,借款期限为48个月。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三年以上至五年(含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逾期罚息为合同约定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40%。杭州世茂公司同时承诺:如发生股权转让、重大资产转让和债权转让以及其他可能对其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事项时,须事先征得杭州世茂公司书面同意。借款人应及时向贷款人报告净资产10%以上关联交易的情况,包括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交易项目和交易性质、交易的金额或相应的比例、定价政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提款条件:先行发放抵押条件项下的人民币开发贷款(总计金额不超过4.6亿元),而后可发放保证人担保条件项下的人民币开发贷款(总计金额不超过3.4亿元)。并约定相应的还款计划。还约定: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贷款人有权单方决定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本息:利用与关联方之间的虚假合同,以无实际贸易背景的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债权到银行贴现或质押,套取银行资金或授信的;出现重大兼并、收购、重组等情况,贷款人认为可能影响到贷款安全等。在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对贷款人的支付和清偿义务等,贷款人可以终止或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等。
2011年4月22日,杭州世茂公司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11NRD002)一份,约定以编号11NRJ017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为本抵押合同的主合同,杭州世茂公司以其名下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1年4月26日办理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杭土抵他项2011第043号)。2015年2月4日,杭州世茂公司又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签订《抵押合同》(编号11NRD003)一份,约定以其名下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及地块上的在建工程为前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于2015年2月10日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杭房建经字第15002743号)。
2011年4月22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编号11NRB023号)一份,约定:由上海世茂公司为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杭州世茂公司签订的编号为11NRJ017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上海世茂公司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进行抗辩。上海世茂公司同时承诺:在杭州世茂公司还清贷款前,不减少和撤回其作为股东对该项目的投入,不进行股东利润分配。
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自行或委托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向杭州世茂公司共发放贷款6.7亿元,具体为:2011年4月29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发放贷款10000万元;2011年5月3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7000万元;2011年5月11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11000万元;2011年6月21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发放贷款8000万元;2011年6月21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6000万元;2011年7月27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3000万元;2011年11月30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7000万元;2011年12月15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发放贷款2000万元;2011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发放贷款7140万元;2011年12月28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2000万;2011年12月29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发放贷款2860万元;2011年12月29日,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发放贷款1000万元。
收到贷款后,杭州世茂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4日、5月27日陆续归还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1.7亿元及利息1553066.67元、本金1.2亿元及利息1725281.89元。对剩余的贷款款项杭州世茂公司未能按期依约还款,遂致成讼。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杭州世茂公司于2009年11月20日注册成立,系上海世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0年3月16日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0万元变更为31000万元,2010年月11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9000万元,2010年7月15日变更为62000万元,2010年8月18日变更为72000万元,2010年11月16日变更为84000万元。2013年6月2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许薇薇变更为蒋明生,2014年11月24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蒋明生变更为张丽芳。杭州世茂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84000万元,系由股东上海世茂公司占资8400万元和皇合公司占资75600万元组成。
本院认为,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杭州世茂公司、上海世茂公司间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11NRJ017)、《抵押合同》(编号11NRD002、11NRD003)、《保证合同》(编号11NRB023),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依法履行各自法定和约定的义务。本案主债务人杭州世茂公司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及主张的债务数额均无异议,故可确认:2011年4月29日至12月29日,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自行或委托中国银行浦东支行向杭州世茂公司共发放贷款6.7亿元;2013年5月24日、27日杭州世茂公司已经归还2.9亿元贷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截止2015年5月31日,杭州世茂公司尚欠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借款本金3.8亿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故依照《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约定,杭州世茂公司应对其未能如期按约返还的剩余贷款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
关于上海世茂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海世茂公司辩称杭州世茂公司已经返还其提供担保的2.1亿元贷款,故无需承担剩余3.8亿元贷款还本付息的连带保证责任。经查,杭州世茂公司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于2011年4月22日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载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向杭州世茂公司发放8亿元贷款,先行发放抵押条件项下的人民币开发贷款(总计金额不超过4.6亿元),而后可发放保证人(上海世茂公司)担保条件项下的人民币开发贷款(总计金额不超过3.4亿元),该合同并无上海世茂公司的签字。从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看,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仅发放了6.7亿元贷款,并未达到8亿元;无证据可区分该6.7亿元中有2.1亿元系由上海世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而由上海世茂公司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上海世茂公司对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上海世茂公司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进行抗辩。虽然上海世茂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经公证的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分别于2013年3月和5月向上海世茂公司发送的“世茂世纪关于股东变更的建议函"和“世茂世纪的股东变更函"的二份邮件及相关还款凭证和电子回单,欲证明其提供担保的2.1亿元贷款已经归还。但鉴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并未放弃依照《保证合同》约定要求上海世茂公司就本案主债权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且相应的还款凭证中也无返还上海世茂公司担保款项的标注,并不能因此排他性地认定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上海世茂公司已就免除上海世茂公司对该2.1亿元贷款的连带保证责任达成合意且已实际履行,故依照《保证合同》中关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的约定,上海世茂公司应对案涉杭州世茂公司未能清偿的3.8亿元贷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上海世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情形及其应否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和鑫源公司、皇合公司应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主张上海世茂公司利用实际控制人身份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并提供了杭州世茂公司、上海世茂公司、牡丹江茂源部分年度报告、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流水明细等。对上述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主张上海世茂公司通过案外人牡丹江茂源抽逃出资,在牡丹江茂源并非本案当事人的情形下其提供的相关证据的证明力无法确认。且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仅提供了杭州世茂公司2010年度的审计报告、牡丹江茂源2011、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和上海世茂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以及部分的资金流水明细,并不能完全印证牡丹江茂源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应收款及杭州世茂公司对牡丹江茂源的应收款以及杭州世茂公司对上海世茂公司的债权之间具有直接对应关系。因此,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海世茂公司抽逃出资,故对其提出的上海世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抽逃出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相应地,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要求上海世茂公司就案涉债务在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提出的鑫源公司和皇合公司明知上海世茂公司抽逃出资仍低价受让杭州世茂公司股份而应对上海世茂公司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杭州世茂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鉴于杭州世茂公司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案涉编号11NRD002、11NRD003的二份《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抵押合同》明确主合同为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和补充,且双方也就《抵押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故可以确认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杭州世茂公司的抵押权设立,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就案涉金融债权对杭州世茂公司名下的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14号路以南、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杭土抵他项2011第043号)以及其上在建工程(杭房建经字第15002743号)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权就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关于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用。案涉《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在杭州世茂公司出现违约时可以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等。《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主债权,包括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等。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主张其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律师费用494万元,并提供了相关的增值税发票及转账凭据,杭州世茂公司、上海世茂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本院综合本案的难易程度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作为原告自身的诉讼能力等实际情况,酌定支持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主张实现债权的200万元律师费用。
综上,杭州世茂公司应依约对其未按期返还的剩余借款承担返还责任和抵押担保责任,上海世茂公司应对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有理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上海世茂公司承担抽逃出资补充赔偿责任和鑫源公司、皇合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因依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世茂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本金3.8亿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利息按照每笔实际提款日中国人民银行施行的三年以上至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的利率标准,从每笔实际提款日计算至该笔借款期届满之日;罚息自借款期届满次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上述浮动利率水平上加收40%计算);
二、被告杭州世茂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实现债权费用200万元;
三、被告上海世茂公司对杭州世茂公司应当支付的本判决第一、二项中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原告中国银行杭州经济开发区支行对抵押物即被告杭州世茂公司名下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14号路以南、25号大街以西的土地使用权(杭土抵他项2011第043号)以及其上在建工程(杭房建经字第15002743号)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驳回原告中国银行杭州开发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171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22134元,由杭州世茂公司负担,上海世茂公司负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2017134元(具体金额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最高人民法院,中央财政汇款专户,账号:××--2003010xxx40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崇文区支行前门分理处。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范启其
审判员 孙光洁
审判员 王 丽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雅倩
某公司与邱某某等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上诉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浙商外终字第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岑某某。
委托代理人:喻某某。
委托代理人:黄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某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某某。
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瞿某某。
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阮某某。
上诉人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被上诉人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商外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岑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喻某某、黄某某,被上诉人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瞿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某公司于1996年3月28日经工商行政管甲门核准登记成立,成某某邱某某担任董事长直至2007年5月。钱某某在某公司成某某即担任总经理,直至2008年11月29日向乙迈特公司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洪某某于1999年9月起担任某公司的财务经理、主办会计。2009年9月11日,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任命洪某某为公司清算组组长。2010年6月1日,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免去洪某某公司清算组组长的职务。某公司股权变更后,股东宁某司伊特电器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20日出具《委派董事通知》,委派陈某某、钱某某担任董事。
某公司成某某注册资本100万美元,分别为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汽轮公司)出资15万美元,海南南亚饮水机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亚公司)出资50万美元,司甲国际有限公司(简称司甲国际)出资35万美元。南亚公司成立于1994年,由台湾南亚饮水机工业有限公司出资83.3万美元,海南南隆工贸联营公司出资35.7万美元,邱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南亚公司经营期截止于2002年1月,于2010年1月28日被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南亚公司1999年-2001年的审计报告显示其对某公司没有应付账款。某公司1997年2月的审计报告和2005年3月的审计报告均显示其对南亚公司没有应收账款,其中1997年2月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南亚保龄球公司向乙迈特公司借款156.4万元为其他应收款。某公司2004年3月及2006年8月的审计报告均显示其对南亚公司有应收款290.5万元。
2007年5月16日,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杭汽轮公司的委托,出具资产审核报告,载明“保留及其他事项说明:其他应收款中南亚公司290.5万元,经核实系公司成某某(1996年)南亚公司对公司投资款,公司成立抽回挂账;报告使用者应考虑资产及负债核实情况中保留事项对公司期末资产及负债的重大影响;本报告仅供杭汽轮公司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事务所无关”。
2010年12月30日,某公司以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在任职期间协助南亚公司抽逃出资290.5万元以及钱某某、洪某某利用职务之便隐匿公司有关会计账簿凭证,为公司查账、追讨账款设置障碍造成公司经营困难并停业损失等理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共同赔偿某公司资本金损失290.5万元,利息损失按每天0.21‰计算,从1996年7月1日起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暂合计为6136434.85元)。
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南亚公司抽回290.5万元资金,事实上该笔资金未抽回。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作为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被其他公司拖欠并没有过错。某公司的股权在2007年转让给其他公司后,某公司有权向拖欠其款项的单位主张权利。请求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本案管辖地问题。因被告钱某某、洪某某的住所地在浙江省杭州市,属于原审法院管辖范围,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案件,对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本案争议的侵权行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之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某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甲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的条件是:1.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为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甲的行为;3.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的行为给某公司造成了损失。首先,邱某某在1996年至2007年期间为某公司董事长,钱某某在此期间为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洪某某在1999年9月起担任某公司财务经理,
javascript:SLC(60597,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乙定的其他人员”之规定,故应确认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为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次,某公司主张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存在抽逃南亚公司注册资金290.5万元这一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主要依据是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16日出具的资产审核报告。虽然该资产审核报告上对290.5万元在“保留及其他事项说明”一项中载明为系公司成某某(1996年)南亚公司对公司投资款,公司成立抽回挂账。但原审法院注意到:第一、本案当事人提供了包括前述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审核报告及1997年、2004年、2005年、2006年某公司审计报告在内的5份证据,4份审计报告均系会计师事务所接受某公司或者某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对某公司资产负债表、会计报表等财务凭证进行独立全面审计所作并在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备案的审计报告,在审计结果中从未指出存在南亚公司抽回注册资金的事实。第二、前述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审核报告仅是某公司的股东之一杭汽轮公司单方委托形成,且资产审核报告中明确指出,报告使用者应考虑资产及负债核实情况中保留事项对公司期末资产及负债的重大影响。本报告仅供杭汽轮公司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事务所无关。说明无论是委托资产审核的杭汽轮公司还是作出资产审核的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均清楚因该报告所作出的资产审核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导致其只能被杭汽轮公司使用而不能被包括某公司在内的其他公司使用,故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并未进行备案。第三,即使南亚公司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系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所为或者协助完成。再次,即使某公司关于南亚公司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之主张甲,鉴于某公司2004年、2006年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披露其对南亚公司有应收款290.5万元,某公司的全体股东对此应当清楚知晓。而是否向甲公司催讨该笔欠款、何时向其催讨、以何方式向其催讨应当由全体股东作出决定,而非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作出决定。即使邱某某是某公司股东之一即司甲国际的法定代表人,毕竟司甲国际并不是某公司的唯一股东。某公司从未向甲公司就该笔290.5万元欠款进行主张,即以南亚公司于2010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认定某公司无法向其主张权利于法无据。由此,不能认定某公司存在290.5万元损失,更不能认定系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的行为造成某公司的损失。至于某公司提出钱某某、洪某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隐匿公司1996、1997年,2006年7-12月,以及其他若干单本的会计账簿凭证,对公司查账、追讨账款设置了障碍之主张,没有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综上,某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有效证据佐证,且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755元,由某公司负担。
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在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三人在任某公司高管期间,弄丢了公司290.5万元,弄丢的性质应是南亚公司抽回出资。原判否认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资产审核报告对该290.5万元系抽回出资的判断错误。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的该审计报告足以认定该款项是抽逃注册资本。虽然资产审核报告载明只能被委托人杭汽轮公司使用,但杭汽轮公司是某公司的股东之一,某公司作为被审核单位使用该报告,符合杭汽轮公司的利益和报告目的。2.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三人同时担任了某公司和南亚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两公司的关某某系以及三被上诉人双重高管身份,足以证明该款项被抽逃是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侵害某公司利益。3.不论290.5万元性质是否属于某某公司抽逃出资,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基于某公司和南亚公司的关某某系和三被上诉人的双重高管身份,某公司账上有对南亚公司的290.5万元的应收款,而南亚公司的账上没有对应的应付款,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也应对其任职管理某公司期间的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原判认为是否向甲公司催讨该290.5万元应由全体股东决定并非三被上诉人作出决定错误。综上,某公司账上少了290.5万元,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均应对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共同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某公司至今无法确定讼争的290.5万元款项性质是什么。该款项到底是南亚公司抽逃出资还是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应收款,还是邱某某等挪用或职务侵占款,某公司上诉提出“弄丢”说法,不是法律概念。某公司对290.5万元款项的性质未能叙述清楚,则其对基本事实不能清楚陈述和明确的情况下,其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2.某公司认为三被上诉人是南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依据不足,其提供的证据材料除显示邱某某是南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外,没有证据证明钱某某和洪某某也是南亚公司的高管人员。3.某公司没有证据表明南亚公司存在抽逃290.5万元出资的行为。如是南亚公司抽逃出资,某公司应提供付款至南亚公司的支付凭证或者南亚公司汇入凭证,但某公司始终无法提供。2004年、2006年审计报告及记账凭证载明对南亚公司有290.5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完全是某公司自行调账的结果,并未得到南亚公司的认可,也与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审计部门于1997年、2005年向乙迈特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自相矛盾。1997年、2005年的审计报告并没有载明对南亚公司有应收款。所有审计报告均没有认定南亚公司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且审计报告由会计事务所出具并经工商备案。4.某公司提供的浙江东方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资产审核报告并不能证明南亚公司抽逃出资。该报告系杭汽轮公司单方委托,只能由杭汽轮公司使用,不能用于其它任何目的,杭汽轮公司及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对该报告均有明显的保留意见或有一定的局限性。5.该290.5万元也不是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应收款。南亚公司的审计报告不仅显示对某公司没有应付款,反而显示对某公司有应收款,1999年为3702805元,2000年为5512556.51元,2001年为6112556.51元。某公司2004年、2006年审计报告显示对南亚公司的应收款为290.5万元,但从其提供的记账凭证看,该290.5万元有某公司对南亚保龄球公司的应收款156.4万元和其它应收款134.1万元合计而成。资产审核报告认为该290.5万元是南亚公司抽逃出资与记账凭证自相矛盾。6.某公司关于该290.5万元是邱某某等被上诉人挪用或职务侵占的款项上诉理由,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与其诉称的是南亚公司抽逃出资或其他应收款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7.即使是南亚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依法应由原股东承担责任,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无任何过错,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即使是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甲公司主张了权利或者无法主张权利,无法证明其存在损失。某公司的现有管理人员未向甲公司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也应承担责任。综上,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自相矛盾,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被上诉人钱某某、邱某某、洪某某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材料。上诉人某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供了杭某某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2006年3月30日、2007年4月25日向乙迈特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杭金会审字(2006)第255号和某某会审字(2007)第447号审计报告。该两份审计报告关于“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注释”内容中均载明对大额户南亚公司有290.5万元的其他应收款。用以证明钱某某、邱某某、洪某某等管理某公司期间的2005年、2006年审计报告,某公司对南亚公司就有290.5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抽逃出资一般均记账为“其他应收款”,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对该款项负有责任。
钱某某、邱某某、洪某某经辨认,对某公司提交的前述两份审计报告的形式真实没有异议,但对该账目的内容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审计报告是某公司单方委托,对南亚公司有290.5万元其他应收款,未经南亚公司确认。此外,从第255号审计报告内容看,某公司总的应收账款为24682576.65元,南亚公司的290.5万元仅为其中的一笔。按照某公司的逻辑,对南亚公司的290.5万元应收款被上诉人作为公司高管人员负有赔偿责任,则对该合计2400多万元的应收款现任公司高管也负有法律责任。
二审庭审以后,某公司又向本院提供了两组证据材料:第一组,南亚公司1997年、1998年董事会会议纪要各一份;南亚公司2001年1月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各两份。用以证明钱某某、邱某某、洪某某分别是南亚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以及财务负责人,具有南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第二组,2011年4月2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执复字第××号执行裁定书一份。用以证明慈溪市人民法院和宁波市人民法院在另案中认可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浙东会专(2007)1061号资产审核报告的证据效力。
本院于2013年6月13日召集双方对某公司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调查质证。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经辨认后认为,对第一组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南亚公司的董事会记录、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均属于某某公司所有,为何某公司持有这些材料,不排除某公司以不合法手段获取;即使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是南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与本案讼争纠纷无关联,该证据材料不能证明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损害某公司利益。对第二组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宁某相关法院在另案中追加星星集团和杭汽轮公司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超越资产审核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且该另案系调解结案的一起虚假诉讼,星星集团和杭汽轮公司已提出再审申请,该执行裁定不能证明本案讼争的资产审核报告具有证据效力。
对某公司庭审中和庭审后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审核认为,邱某某等被上诉人对杭金会审字(2006)第255号审计报告和某某会审字(2007)第447号审计报告的形式真实无异议,具有二审证据资格,至于能否证明某公司的证明目的,是双方讼争的本案焦点,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在裁判理由部分阐述。对某公司庭后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有原件可以核对,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虽对其来源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没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故具有证据资格,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从该组证据内容反映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曾是南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但三被上诉人是否具有南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与本案讼争焦点三被上诉人是否侵害了某公司利益不具有关联性。某公司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形式真实可以认定,但该裁定书系相关法院在其他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出具的裁定书,该裁定书追加案外人为被执行人与本案纠纷不具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某公司2002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记载,某公司对南亚保龄球公司有156.4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将其总户中的另134.1万元其他应收款,合计调整为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其他应收款290.5万元。3.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形式真实无异议的杭某某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3月30日、2007年4月25日向乙迈特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杭金会审字(2006)第255号和某某会审字(2007)第447号审计报告内容记载,某公司对南亚公司有290.5万元的其他应收款,但均未载明该款项系南亚公司抽回的注册资本。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邱某某系台湾居民,故本案应参照涉外案件审理。本案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纠纷,属于侵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协议选择法律适用,但由于起诉的侵权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本院确认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正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是否应对某公司主张的290.5万元款项承担赔偿责任,其中涉及:该款项性质是什么;如果是南亚公司抽逃的出资,三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协助抽逃出资的情形;如果是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三被上诉人是否存在阻扰或妨碍某公司向甲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形。评析如下:
邱某某、钱某某和洪某某曾是某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财务经理,具有某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条件有:一是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甲的规定;二是执行职务的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综合全案有效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某公司要求邱某某、钱某某和洪某某赔偿讼争的290.5万元及其相关利息,依据不充分。主要理由:
一、难以认定讼争的290.5万元是南亚公司抽逃的出资。1.从该290.5万元款项的来源和组成看系经某公司调账而成,并非某公司直接支付南亚公司。某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2002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记载,某公司将其对南亚保龄球公司的156.4万元其他应收款和总户中的另134.1万元其他应收款,合计调整为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其他应收款290.5万元。从法律角度,该调账应属债务转移,是南亚保龄球公司和总户中的其他单位将各相关债务合计290.5万元转移给南亚公司承担,但某公司没有提供原始凭证证明该调账经相关当事人协商一致。2.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仅凭某公司提供的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向杭汽轮公司出具的浙东会专[2007]1061号资产审核报告,不足以认定南亚公司抽逃290.5万元出资。诉讼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多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多份审计报告。某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杭某某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2004年3月25日、2006年3月30日、2007年4月25日向乙迈特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杭金会审字(2004)第268号、杭金会审字(2006)第255号、杭金会审字(2007)第447号审计报告,仅载明某公司对南亚公司有290.5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未指出该其他应收款系南亚公司抽逃出资。而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某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的浙瑞会计师事务所于1997年2月向乙迈特公司出具的浙瑞所审字[1997]012号审计报告、杭某某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3月向乙迈特公司全体股东出具的杭金会审字(2005)号第311号审计报告,即未载明南亚公司有积欠某公司款项,也未载明某公司对南亚公司有其他应收款,更未载明南亚公司抽逃出资。其中,浙瑞所审字[1997]012号审计报告载明某公司对南亚保龄球公司有156.4万元的其他应收款,与某公司提供的2002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载明的内容能相互印证。可见,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前述1997年、2004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向乙迈特公司或者全体股东出具的五份审计报告中,均没有关于南亚公司抽逃290.5万元出资的内容。某公司提出抽逃出资一般记载为“其他应收款”并无依据。此外,某公司提供的浙东会专[2007]1061号资产审核报告具有一定局限性,一是该报告系受某公司的股东杭汽轮公司的单方委托而出具,并非受某公司或全体股东委托;二是该审核报告在“保留及其他事项说明”中认为讼争290.5万元经核实是南亚公司在某公司成立后投资款抽回挂账。但对“经核实”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确凿充分,未作进一步列明;三是该报告对使用范围作出限定,该审核报告在“其他主要事项说明”中载明,报告仅供杭汽轮公司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四是该资产审核报告并非经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报告。3.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南亚公司的相关审计报告没有载明某公司有290.5万元款项汇入。南亚公司作为某公司主张抽逃出资的被诉对象,未参与本案诉讼,但因邱某某也系南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了海南华合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于1999年1月18日、2000年2月1日向甲公司出具的海华合会审字[1999]第006号、海华合会审字[2000]第011号以及海南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1年2月18日向甲公司出具的方正所审字[2001]第010号审计报告作为反驳证据。虽然某公司在质证时对该三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原审庭审中某公司核对了原件,也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该三份报告的形式真实性可以确认,南亚公司的前述审计报告不仅均没有载明南亚公司积欠某公司款项,相反,载明南亚公司对某公司有数百万元的其他应收款。综上,某公司认为南亚公司抽逃290.5万元出资的诉讼主张,依据不足,也与其提供的2002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反映的内容不符。
二、某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邱某某、钱某某和洪某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阻碍某公司向甲公司主张290.5万元的行为。
从某公司单方提供的现有证据看,该290.5万元是某公司对南亚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不论该讼争款项性质是某公司主张的南亚公司抽逃的出资还是对南亚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某公司均可依法向甲公司主张权利。南亚公司虽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并未注销,从法律角度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现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向甲公司依法主张权利或起诉,也没有证据证明邱某某等三被上诉人存在阻扰或妨碍某公司向甲公司主张权利的行为。
此外,某公司还主张该290.5万元款项是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利用职务侵占或挪用的款项,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某公司要求邱某某、钱某某、洪某某赔偿290.5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755元,由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徐向红
审判员张士冬
代理审判员孙伊涵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章瑜
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等与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上诉案
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等与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上诉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浙民终6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明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
诉讼代表人:盛杰,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杰,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莹,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广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分公司)、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资产公司)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商初字第30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际广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寅,被上诉人温州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杰,被上诉人国贸资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际广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温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温州分公司负担。上诉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1)温州分公司提交的证据6、7与案件事实不符,原审判决采纳其证据6、7属于对证据的认定错误。第一,温州分公司的证据7《资产评估报告书》没有原件,国际广告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二,温州分公司主张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只提供了证据6、7这两份报告加以证明,但该两份报告都是受温州分公司自身的委托对其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第三,证据6《资产清查审计报告》只是在文字中描述“1995年由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增拨资本金1845650元,实收资本增至2000000元,但当年省公司就抽回资本金1845650元,挂账于其他应收款。”证据7《资产评估报告书》也是在文字中描述“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投资给国广温州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其中1845650元已抽回,至今未到位。”温州分公司未提供任何实际付款凭证证明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回资本金的行为。鉴于温州分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温州分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即破产管理人掌握和占有温州分公司的财务账册,但未能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国际广告公司抽逃出资的财务上的证据。第四,作为《资产清查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其记载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资本金的事实,必须要有相应的支付凭证证明。温州分公司在庭审时提供的《资产清查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仅仅是复印件,直至本案一审判决前几天,温州分公司才让当时的审计单位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公章,证明其真实性。既然审计单位加盖了公章,其审计材料中必然有国际广告公司抽回注册资本的相应支付凭证。但至今,温州分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该注册资金的支付凭证。第五,其他应收款会计科目是指企业在商品交易等经营活动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的款项,是指应收而还未收到的款项。如果按照温州分公司的主张,本案中存在先投入资本金后又抽回的情况,按照会计准则是不能够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因此,温州分公司的证据6和证据7既不符合本案事实,也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不能证明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回资本金的行为。(2)原审判决应当采信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5和证据9。第一,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5是温州分公司自己向工商局提交的关于变更为独立法人的申请材料,包括温州分公司在成为独立法人以后的法人章程以及温州分公司委托温州建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告经营资质检查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广告专项审计报告》),这份报告的委托人与温州分公司证据6、7的报告委托人相同,都是温州分公司本身。同样都是温州分公司委托第三方出具的评估或审计报告,在国际广告公司除这份《广告专项审计报告》以外还提供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仍只认可温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6和证据7,但对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报告和其他证据一概不予认可,显然是对证据片面和错误的认定。第二,温州分公司的法人章程第十条载明“本企业注册资金来源为省国际广告公司投资200万元。”《广告专项审计报告》第1条载明“贵公司注册资产为200万元,1997年账面实收资本为200万元,由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投入。”以上可以证明在1997年末国际广告公司对温州分公司的注册资金投入为200万元,不存在抽逃的情况。第三,国际广告公司证据9是温州分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年检材料,温州分公司自行制作的材料,与股东国际广告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原审判决认为,工商部门对工商年检报告书其中的资产负债表等资料仅作形式审查,即全面否定年检材料的证据效力,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没有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温州分公司和国际广告公司在90年代时均是国有企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温州分公司向工商年检部门提交的年检材料是不可能造假的,也没有必要造假。原审法院以现在的观点要否定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证据效力,明显没有说服力。证据9年检材料不仅能够证明温州分公司自1995年起实收资本一直为200万元,更能证明其每年的其他应收款余额。根据温州分公司历年年检报告书显示,其自1994年至1999年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706225.85元、127202元、1069080.03元、961758.50元、1467536.15元、1371790.85元,始终小于1845650元。因此温州分公司主张国际广告公司在增资的当年,即1995年在增资后又将1845650元抽回,并挂账于其他应收款科目,完全不符合案件的基本事实。以上事实足以反驳原审判决中关于“但不能说明这实收资本中不包括其他应收账款的项目在内”的认定。既然那么多年的其他应收款都远远小于1845650元,温州分公司主张的国际广告公司在抽回出资的同时又挂账于其他应收款又怎么可能成立?因此,结合国际广告公司的证据5、证据9以及证据4,能够证明国际广告公司在1995年对温州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1845650元,并且实收资本在1995年以后始终保持在200万元,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的行为。2.原审判决对法律适用和认定存在错误,关于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案件事实上,国际广告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国际广告公司自1995年对温州分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1845650元后,温州分公司的实收资本金始终为200万元,其他应收款余额也一直小于1845650元,因此显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广告公司抽逃出资,后温州分公司挂账于其他应收款的行为。(2)从举证责任上,温州分公司应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但温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不足。温州分公司证据6和证据7只是在文字上记载了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并且该两份报告内容也不相同,证据6《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认为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资本金并挂账于其他应收款,而证据7《资产评估报告书》只简单描述国际广告公司的投资款已抽回,但对如何抽回没有进行说明。温州分公司在本案起诉时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财务凭证证明国际广告公司具体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抽回该1845650元增资款,而具体财务凭证才能证明抽回资本金的行为,仅凭两份财务报告不具有足够的证明力。从举证责任分配上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的当事人应该对该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温州分公司认为国际广告公司投入注册资本金后又抽回了注册资本金,必须要证明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该资本金的相关证据。该证据应该是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该注册资本金的付款凭证,而不是温州分公司自行委托审计报告中的一段字面描述即可,该段描述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在本案中,首先应当由温州分公司作为原告充分举证证明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只有当温州分公司尽到了充分的举证责任,才需要由国际广告公司来举证进行反驳。但是本案中温州分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相反国际广告公司已经尽力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因此原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存在错误。(3)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已足以反驳温州分公司的证据,足以证明国际广告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依前述,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4、证据5、证据9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国际广告公司作为温州分公司的股东在1995年追加投资资本金1845650元,同时不存在温州分公司主张的抽逃出资的行为。退一步说,如果法院认为双方提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各自的主张,按照优势证据原则,结合上述的举证责任分配,法院也应当采信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而不是简单地全部否定国际广告公司的证据而采信温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综上,法院采信温州分公司证据,而不采信国际广告公司的证据,从而认定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3.即便法院认定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鉴于温州分公司在改制时已将债权债务全部剥离给国贸资产公司,因此温州分公司也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无权向国际广告公司主张追收抽逃出资的责任。第一,国际广告公司已提供证据6-8证明在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时,浙江省财政厅已于2000年12月将温州分公司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剥离给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并由该公司承接温州分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后经数次股东变更和更名,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现仍存续,但名称已改为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第二,温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7第二条载明该报告书的评估目的是根据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浙外经贸国资(2003)03号《关于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资产评估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为完成温州分公司企业改制而进行资产评估,更能证明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即国贸资产公司的前身在主导温州分公司的企业改制,并已实际接收和承继温州分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此可见,鉴于温州分公司的债权已经由国贸资产公司所承继,即使本案国际广告公司存在归还抽逃出资款项的义务,也应由国贸资产公司向国际广告公司进行主张,温州分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此外,即使本案中国际广告公司负有返还投资款的义务,该返还义务应由国贸资产公司所继受承担,国际广告公司已尽到充分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将国贸资产公司追加为第三人,但认为国际广告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本案原判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支持国际广告公司上诉请求。
温州分公司辩称,1.温州分公司已经提供有效证据可以证明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两份审计报告可以证实温州分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中温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虽然是复印件,但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证实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国际广告公司一审时也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认定,现在其认为本案关键证据是复印件的陈述不符合事实。2.国际广告公司认为举证责任在温州分公司的陈述缺乏依据,温州分公司已经提交了审计报告,且由有资质的单位作出。国际广告公司提交的广告专项审计报告,温州分公司也发表过意见,认为缺乏真实性。广告专项审计报告作出的单位缺乏资质及公正性和客观真实性,仅依照广告资质审计不能推翻温州分公司提交的两份审计报告。对于年检报告,真实性有欠缺,也不能作为证据。一审法官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认定无误,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国贸资产公司辩称,1.对于上诉状一、二部分国际广告公司抽逃出资的陈述,与国贸资产公司无关,国贸资产公司也不清楚相关事实。故对此不发表意见。2.对于上诉状第三部分的意见,根据一审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国际广告公司主张的温州分公司资产与负债已经剥离给国贸资产公司,且国际广告公司在二审中未提出新的证据支持该主张,故原审法院关于第三人的认定是正确的。3.国际广告公司混淆了两种不同资产转让的概念,国际广告公司在一审中的论述与上诉意见对于案涉资产转让方式到底是温州分公司作为转让主体将资产转让给国贸资产公司,还是国际广告公司作为主体将其对温州分公司享有的投资权益转让给国贸资产公司的概念是混淆的,从而得出国贸资产公司既承接了温州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又承接了国际广告公司的债权债务,国贸资产公司既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也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即涉嫌抽逃出资的责任主体的矛盾结论。
温州分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温州分公司系从事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发布外商来华广告业务以及内外销产品包装、装潢等业务的企业。2014年10月22日,温州中院根据上海华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依法裁定受理温州分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4年10月30日依法指定管理人。温州分公司根据国际广告公司(91)浙国广字第19号报告及浙江省外经贸厅的相关批复依法成立并于1991年8月22日领取营业执照。依照相关规定,温州分公司成立的资金数额为20万元,同时国际广告公司系其投资主体。1996年5月17日,温州分公司再次根据国际广告公司的相关规定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享受独立的经营及民事主体资格,并将注册资本依法增至200万元。依照温州建诚会计师事务所于1995年7月19日出具的验资报告显示,上述20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1845650元虽已由国际广告公司出资到位,但国际广告公司却在同年度又将上述出资抽回而将其挂账于其他应收款中,至今仍未返还。综上,国际广告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明显违法且已严重侵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温州分公司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国际广告公司向温州分公司一次性返还18456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199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暂计233527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国际广告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温州分公司于1991年7月2日经批准设立,注册资金为20万元,后经批准增资至200万元,并经温州建诚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已经全部到位,其增资变更登记于1995年8月8日被核准,温州分公司是国际广告公司的分支机构。温州分公司于1998年4月3日经核准变更登记为独立企业法人,国际广告公司持有温州分公司100%股权。2003年6月23日,浙江正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温州分公司委托对温州分公司因清算、改制而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后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国际广告公司投资给温州分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其中1845650元已抽回,至今未到位。”2004年4月7日,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温州分公司委托对温州分公司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全面清查后出具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载明“1995年7月19日经温州建诚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由国际广告公司增拨资本金1845650元,实收资本增至200万元,但当年国际广告公司就抽回资本金1845650元,挂账于其他应收款中。”第三人原名称为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于2003年6月4日变更为浙江荣大资产管理公司,又于2009年7月28日变更为国贸资产公司。
另查明,温州中院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2014)浙温破(预)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上海华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作出(2014)浙温破字第6-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分公司的管理人。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国际广告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以及是否应返还相应款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等情形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温州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国际广告公司将1845650元款项增资到位后又转出,并挂账于其他应收款中,虽然该行为发生时,温州分公司是国际广告公司的分支机构,但在温州分公司成为独立法人后,该款项一直未能返还,客观上构成了抽资的后果。现国际广告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反驳温州分公司的主张,故温州分公司主张国际广告公司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之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国际广告公司以浙江省财政厅出台的批复中载明温州分公司的资产与负债已经剥离给第三人为由,主张其不应承担返还责任,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故温州分公司请求国际广告公司向其返还出资1845650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由于国际广告公司转出1845650元资金的行为发生时,温州分公司系其分支机构,并挂账为其他应收款,款项性质不明,也没有证据证明需要计收利息。故温州分公司主张从1996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对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部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款项184565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247元,由浙江省国际广告公司温州分公司负担22480元,由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7767元。
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国际广告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及是否应当返还出资本息。从温州分公司举证看,其证据主要是其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两份报告书。一份是浙江正大资产评估公司2003年6月23日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复印件,载明“国际广告公司投资给温州分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其中1845650元已抽回,至今未到位。”另一份是温州华明会计师事务所2004年4月7日出具的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载明“当年国际广告公司就抽回资本金1845650元,挂账于其他应收款中。”该两份报告书虽未附相关财务凭证,但对于国际广告公司抽回资本金的结论意见是一致的,温州分公司对其诉讼主张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国际广告公司上诉认为其提交的温州分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和历年年检报告书两份反驳证据可以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经查,该两份证据载明温州分公司的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为200万元,但该记载并不能证明国际广告公司未有抽回资本金的行为。温州分公司历年年检报告书虽然记载的应收款余额均小于1845650元,但应收款余额系应收款与应付款相抵后的记载数额,抵扣后有可能发生应收款余额小于抽回资本金数额的情形,故应收款余额的记载也不能直接推翻资产清查审计报告载明抽回资本金挂账于其他应收款的情形。国际广告公司的该两份证据并不足以反驳温州分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国际广告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47元,由浙江省国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培良
审 判 员 梅 冰
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
王文年等诉温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等抽逃出资纠纷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浙民终7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年。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英龙、毛利忠,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阮臣娒,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双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继伟,浙江瑞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姜刚明。
原审被告:王成标。
原审被告:李红棋。
原审被告:陈承衡。
上诉人王文年因与被上诉人温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峰公司)、原审被告姜刚明、王成标、李红棋、陈承衡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商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文年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标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标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纵观全案,并无证据证明王文年抽逃出资的事实,原审法院仅以个别且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陈述为依据认定该事实,显属错误。本案中的证据也能证明王文年与标峰公司已经达成退股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文年已与标峰公司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标峰公司要求王文年返还投资款没有依据。(一)原审认定王文年抽逃出资款11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调取的自筹资金走向的证据,不能证明王文年抽逃出资。该证据显示:各股东出资款到位后,王成标将出资款转到其个人账户,后又转到危平账户,危平进行了提现及转账。上述转款行为均与王文年无关,王文年对转款情况不知情。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转款行为为抽逃出资,更不能证明王文年抽逃出资。2.仅以个别有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陈述,不能证明王文年抽逃出资。虽然王成标陈述标峰公司的出资系向融资公司借款垫资,公司设立后即归还,但并未得到其他股东的认可。3.王文年提供的证据可证明各股东出资10万元是为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投资的项目,该出资与标峰公司的成立无关,不是标峰公司的出资款。(二)王文年已经退股,不应承担出资的相关法律责任。王文年提供的《退股协议书及证明》等证据,可证明王文年2011年已退股,无论标峰公司在收购王文年股权后是否在股东之间重新分配,无论该股权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均不影响王文年已在公司内部已经退股的事实。(三)标峰公司及其管理人起诉事实前后混乱,工作不严谨,其诉请应予驳回。标峰公司及其管理人在未查清公司实际出资事实的情况下,迳行起诉要求王文年补缴出资,为调查了解公司的出资已到位并经验资等客观事实,在法庭释明后,才按法庭的要求调整其主张。标峰公司最初起诉时,仅将王文年列为被告,其他股东为案外人,在法庭告知后,又追加其他股东为被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上述均表明标峰公司财务混乱,管理人工作不严谨、不尽责,接管、交接不齐全,并滥用职权。
标峰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文年向标峰公司补缴未到位出资款11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94%,自2009年3月31日起算至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暂算至2015年4月30日为39.7485万元);2.王文年对其他股东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共计855.39075万元向标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王文年承担。2015年9月18日,标峰公司申请追加股东王成标、李红棋、陈承衡、姜刚明为被告,并以其他股东未出资额另案主张为由,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王成标、李红棋、陈承衡、姜刚明对王文年未足额出资的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3月24日,王成标、王文年、金钦勋、李红棋、陈承衡、姜刚明为成立标峰公司,共同签订《温州标峰建设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四章“股东名称(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和出资时间”中第十一条约定王成标实缴出资200万元,已于2009年3月31日全部到位;王文年实缴出资120万元,已于2009年3月31日全部到位等。标峰公司的内账记录上载明于2009年3月15日收到王文年投资款10万元。王文年借款筹到120万元出资款,会同其他各股东于2009年3月31日将出资款现金存入标峰公司账户,通过验资后,于2009年4月2日将该800万元的出资款全部转到王成标个人账户,王成标于同日再将该800万元出资款转到危平个人账户,危平同日通过现金取款以及汇款的方式收取了该800万元。2013年9月11日,原审法院裁定受理标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3年9月17日作出民事决定书,指定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标峰公司管理人。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王文年作为标峰公司的股东,不仅应当履行出资义务,且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已经查明王文年于标峰公司成立之时将120万元出资款存入标峰公司,应视为其已经尽到出资义务,标峰公司依据内账记载的王文年出资10万元的事实而主张追收未缴出资纠纷应属不当,本案案由应为抽逃出资纠纷。标峰公司经法院就法律关系进行释明之后,亦同意变更为抽逃出资纠纷主张其诉请,故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王文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110万元的事实;二是王成标、李红棋、陈承衡、姜刚明是否应对抽逃出资款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王文年于2009年4月2日抽逃出资款110万元,理由如下:1.标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即王成标在接受谈话时承认“每个股东都是出资10万元,因为登记需要800万元,再另外向融资公司借款垫资,公司设立后就将该笔款项还回去了”,与依标峰公司申请调取的银行明细内容可以印证,证实王文年的出资款通过验资后,抽回出资款至王成标名下,由王成标操作偿还借款。2.标峰公司提供的公司内账显示王文年在公司尚存的出资款为10万元,该记载不仅与王成标陈述的股东出资情况相吻合,也与王文年首次接受谈话时陈述的“出资是10万元”相一致。3.王文年认为其已经退股,股权转让给标峰公司,无论出资是否到位均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回购本公司股份为原则,只有“减资、奖励本公司职工、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股东反对和公司合并分立”等四种情形为例外,王文年主张的退股不符合上述的四种例外情形,且并未及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如120万元出资款在未抽逃的情况下退股,却不在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也从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明显不符情理,不予采信。因王文年抽逃出资的时间为2009年4月2日,故利息损失应当从该日起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成标应当对王文年抽逃出资款11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本案目前的现有证据看,800万元出资款验资后均是流入王成标的个人账户,再通过王成标操作转入案外人危平账户,案外人危平以取现或转账的方式收取该800万元,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股东姜刚明、李红棋、陈承衡有协助抽逃出资的情形。故王成标协助王文年抽逃出资110万元,应当对该110万元出资款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标峰公司的诉请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6月28日判决:一、王文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标峰公司返还其抽逃出资款11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09年4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王成标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标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8277元,由王文年、王成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文年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标峰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2014年10月8日,阮臣娒、吴双节与王成标的谈话笔录,证明:标峰公司实际出资只有61.66万元,工商部门登记800万元的注册资本系垫资款的事实。2.银行存单、存款凭单、取款凭条、现金缴款单等,证明:800万元的注册资本系垫资的事实。
被上诉人王文年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此外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谈话笔录中,对王成标陈述的内容是否为本案客观事实存疑。王成标陈述的垫资、各股东出资数额亦未得到其他股东的认可。至于公司的经营项目情况,与本案无关。从证据的合法性看,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王成标系本案当事人,应出庭接受询问,否则不应具有证明力。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垫资事实的存在,也非标峰公司所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仅以银行存单上的流水号证明垫资的事实。如要证明垫资,应当由标峰公司提供其他诸如投资合同相关等相关证据加以佐证,或由法院对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垫资的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为:标峰公司提交的证据,王文年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可认定其具有证据资格,至于能否证明垫资的事实,将结合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认定王文年抽逃出资的证据是否充分;王文年的退股事实是否成立,其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标峰公司设立于2009年3月31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依照标峰公司章程的规定,王文年应出资120万元。2009年3月15日,标峰公司向王文年出具收款收据,收到投资款10万元。2009年3月31日,温州东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温东成会验字〔2009〕222号验资报告,证实王文年实际缴纳出资额为120万元。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分户明细反映,2013年3月31日户名为标峰公司的2010xxx32616账号王文年现存投资款120万元,同年4月2日该账户中包括王文年在内的800万元出资款分次汇入王成标账户后转汇危平账户。原审法院认定王文年抽逃出资,有相应依据。理由是:1.王成标于2016年1月18日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证实王文年仅出资10万元,标峰公司注册资本中的800万元系融资垫资,在公司设立后已归还。2.王文年2016日1月19日接受原审法院询问时,承认其出资为10万元,虽然原审庭审中主张其出资120万元,但至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3.标峰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可证明标峰公司验资的800万元来源于胡珺的存单等,后该款在同一时间内作为标峰公司股东的出资。在完成验资后,上述款项先转入王成标账户,再通过危平账户转为胡珺的存款。标峰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证明标峰公司的注册资本被抽逃的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王文年存在抽逃出资的证据充分,王文年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王文年虽提交了其与标峰公司的《退股协议书》,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标峰公司,但该行为因违反了前述禁止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应认定无效。原审法院据此判令王文年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法律依据。
综上,王文年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77元,由王文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忠良
代理审判员 周进海
代理审判员 倪佳丽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吕 俊
张颖斐等诉张松伟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再审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浙民再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颖斐。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辉,杭州市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刘旭海,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玲,浙江新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蓉蓉,浙江新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松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绍平。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洁。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温州阿尔凡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洁,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四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林松,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姜晓东。
再审申请人张颖斐与再审申请人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莱公司)、被申请人张松伟、张绍平、郑洁、温州阿尔凡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尔凡公司)、姜晓东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两再审申请人均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商终字第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231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颖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光辉,再审申请人柏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玲,被申请人张松伟、张绍平、郑洁、阿尔凡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松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姜晓东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市洞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温州柏莱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莱服饰公司)于2005年4月29日经批准为中外合资企业,2005年5月11日工商核准登记,注册资本210万美元,其中张颖斐出资94.5万美元,张松伟出资42万美元,张绍平出资73.5万美元,张颖斐为董事长,张松伟为董事,张绍平为副董事长。张颖斐于2005年6月29日缴纳出资220万元、2006年12月5日缴纳出资45万元、2006年12月11日缴纳出资139.08万元和200万元、2006年12月13日缴纳出资106万元、2006年12月18日缴纳出资41万元、2006年12月19日缴纳出资1万元和600元、2006年12月20日缴纳出资46万元和487.08万元。公司于2006年12月11日转出139.08万元、2006年12月19日转出487.08万元、2007年2月13日转出250万元、2007年5月22日转出50万元到张颖斐账户。公司以内衣款名义分别于2006年12月25日支付106.3万元、2006年12月28日支付110.88万元、2006年12月30日支付82.41万元给姜晓东。公司以货款名义于2007年2月13日支付150万元给郑洁。公司以支付材料款名义于2005年12月21日和2005年12月23日各支付1571875.50元、327606.30元给阿尔凡公司。2009年7月6日,香港时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时运公司)分别与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书,由香港时运公司受让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持有柏莱服饰公司全部股权。2010年3月29日经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柏莱服饰公司名称变更为柏莱公司。2010年8月3日张松伟、郑洁、张绍平通过阿尔凡公司账户汇款400万元给柏莱公司。2013年7月25日一审法院受理柏莱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同时指定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现名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柏莱公司破产管理人。
柏莱公司于2014年3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柏莱服饰公司于2005年4月29日经批准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210万美元,其中张颖斐出资94.5万美元,张松伟出资42万美元,张绍平出资73.5万美元,张颖斐为董事长,张松伟为董事兼总经理,张绍平为副董事长。2009年7月6日香港时运公司与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分别签订企业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他们持有的柏莱服饰公司全部股权,2010年3月29日经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柏莱公司,注册资本210万美元不变。2013年7月25日一审法院受理柏莱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同日指定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现名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柏莱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查明公司资产只有1880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尚未竣工厂房)。从公司财务发现:一、张颖斐缴纳出资的累计余额为3590600元,依照验资报告张颖斐两次出资220万元和5311106.50元合计7511106.50元,张颖斐以转入又转出方式抽逃出资3920506.50元。二、张颖斐以预付姜晓东针织内衣货款名义,开出三张现金支票,累计金额为2995900元,但没有相应合同、发票、入库单及账面存货记载,况且柏莱公司自成立以来并未生产,姜晓东系张颖斐丈夫。上述款项系张颖斐以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及关联交易方式抽逃出资。三、张松伟以购货款服装名义开具金额为150万元现金支票给郑洁,但同样没有合同、发票、入库单及账面存货记载,郑洁系张松伟妻子。上述款项系张松伟以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及关联交易方式抽逃出资。四、张绍平以购材料名义开具1899481.80元的银行本票给阿尔凡公司,但同样没有合同、发票、入库单及账面存货记载,阿尔凡公司副董事长为郑秀燕,郑秀燕系张绍平妻子。上述款项系张绍平以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及关联交易方式抽逃出资。香港时运公司受让股权后,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均未补缴上述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同为公司发起人和董事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因为股权转让而免除其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因债务人虚构债务的行为无效,姜晓东、郑洁、阿尔凡公司依法负有返还实际占有的上述债务人财产。故请求判令:1、张颖斐向柏莱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本金3920506.5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本金920506.50元从2006年12月19日起、本金250万元从2007年2月13日起、本金50万元从2007年5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张颖斐、姜晓东共同向柏莱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本金299590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本金1063000元从2006年12月25日起、本金1108800元从2006年12月28日起、本金824100元从2006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张松伟、郑洁共同向柏莱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本金15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7年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4、张绍平、阿尔凡公司共同向柏莱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本金1899481.8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5年12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5、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责任。
张颖斐、姜晓东一审辩称:一、张颖斐、姜晓东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2007年2月15日温州诚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明确指出,公司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美元21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公司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二、本案股权转让的实际情况。原公司股东将公司全部股东权益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公司所有权转给孙福财,债权、债务风险由孙福财承担。柏莱公司的管理人系柏莱公司审计主体,其隐瞒了公司为获取土地使用权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仅仅以股东投资额与支出额作简单的加减,得出的数额即推定是抽逃出资,不符合客观事实。若该主张成立,股份转让价款为1250万元,还要返还1032万元及利息500万元,则整个公司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全部送给柏莱公司,还要倒赔几百万元,这显然不合常理。公司账册均由管理人接管,无法取得真实有效的账目凭证。三、张颖斐、姜晓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与柏莱公司破产案件受理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根据2007年2月15日温州诚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记载,张颖斐已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公司股权转让前后,公司性质、主体已发生根本变化,公司股权转让之前,对外没有任何负债,亦没有损害破产债权人的利益,现股权转让之后产生新的债务导致公司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与原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性。综上,柏莱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张松伟、张绍平、郑洁、阿尔凡公司一审辩称:一、不存在抽逃出资3399481.80元(150万元和1899481.80元)的事实。二、柏莱公司实际投资人孙福财的210万元美金没有出资到位。三、根据2011年度柏莱公司的年审报告材料,充分证明柏莱公司没有发生亏损。四、柏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孙福财涉嫌挪用资金罪和虚假破产罪。五、柏莱公司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争议焦点在于各被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柏莱公司认为张颖斐抽逃出资3920506.50元,提供现金支票4份及进账单1份,其中两份用途为退投资款4870800元,该款已于次日汇入柏莱服饰公司的其他账户,剔除该款项往来,张颖斐出资累计达7981400元,已超出章程规定出资额7511106.50元,故对柏莱公司认为该两笔4870800元系抽逃出资的事实,该院不予采纳。对其他三笔分别为139.08万元、250万元、50万元,共计439.08万元,张颖斐承认收到该款项,但认为系替原柏莱公司购买货物,柏莱公司予以否认。张颖斐辩称有关单据在柏莱公司处,经庭审释明,其不申请对账目进行审计。该院现无法查明款项的用途系为购买货物还是抽逃出资,张颖斐身为原公司董事长,其辩称有违常理。根据举证规则,应由张颖斐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现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扣除其多出资470293.50元,可以认定张颖斐有抽逃出资3920506.50元的事实。柏莱公司认为张颖斐、姜晓东抽逃出资2995900元,三方都认可款项系姜晓东收取,但姜晓东辩称款项用途系原柏莱公司向其购买针织内衣;柏莱公司认为张松伟、郑洁抽逃出资150万元,郑洁辩称款项用途系原柏莱公司向其购买服装;柏莱公司认为张绍平、阿尔凡公司抽逃出资1899481.80元,阿尔凡公司辩称款项用途系原柏莱公司向其购买材料。柏莱公司对上述被告辩称都不予认可。由于收款人均非公司股东,其辩称的买卖关系也是正常商业行为。经庭审释明,双方都不申请对账目进行审计,现无法查明款项的用途系为购买货物还是抽逃出资。根据举证规则,应由柏莱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各被告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对柏莱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张颖斐、姜晓东、张松伟、郑洁、张绍平、阿尔凡公司抽逃出资的事实,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张颖斐缴纳出资后的资本所有权已转移为柏莱服饰公司财产,其无权对出资资本进行处置,虽然其抽逃出资时公司并没有债务产生,但抽逃行为侵犯了公司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抽逃出资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柏莱服饰公司变更为柏莱公司后,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继受。故对柏莱公司要求张颖斐返还抽逃出资3920506.50元及利息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利息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抽逃之日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对柏莱公司要求张松伟、张绍平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其未能举证他们有协助张颖斐抽逃出资的行为,结合张颖斐在公司任董事长,又是主管财务,抽逃出资一般无需其他股东协助,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张颖斐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柏莱公司抽逃出资3920506.5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以1390800元从2006年12月11日起、2029706.50元从2007年2月13日起、50万元从2007年5月22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为止)。二、驳回柏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3891元,保全费5000元,由柏莱公司负担75731元,张颖斐负担43160元。
柏莱公司与张颖斐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分别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柏莱公司上诉称:一、张颖斐以预付针织内衣货款名义三次从柏莱公司合计转出2995900元给姜晓东的行为、张伟松2007年2月16日从柏莱公司以购货款名义开具150万元现金支票给郑洁的行为以及张绍平以购材料名义从柏莱公司转出1899481.80元给阿尔凡公司的行为均应依法应认定为抽逃出资。1、上述款项的转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取决于柏莱公司与相对方(姜晓东、郑洁、阿尔凡公司)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该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张颖斐和姜晓东、张伟松和郑洁以及张绍平和阿尔凡公司。但张颖斐和姜晓东、张松伟和郑洁以及张绍平和阿尔凡公司并未就上述争议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甚至连交易的具体事实等均不能说明清楚,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所谓交易的具体行为主体间存在特殊关联关系。即,张颖斐与姜晓东、张松伟与郑洁均是夫妻关系。阿尔凡公司董事长为郑洁,副董事长为郑秀燕。郑秀燕是张绍平的妻子。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之规定,只要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款转出就应认定为抽逃出资。此时,关联交易的另一方并非一定是公司股东。3、姜晓东、郑洁、阿尔凡公司均承认收到相关款项。4、张松伟与郑洁以及张绍平与阿尔凡公司举证了中国银行400万元进账单,欲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并辩称“实际投资人孙福财的210万美元没有出资到位”,由此可见,张松伟和郑洁已经自认抽逃出资150万元,张绍平和阿尔凡公司自认抽逃出资1899481.80元。二、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依法应对上述抽逃款项互负连带责任。1、三人是公司发起人,三人均存在抽逃出资行为。2、三人同时为公司董事和高管,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3、上述抽逃出资行为均通过银行开具支票或本票方式进行。三人均有加盖公司印章和法人私章,张颖斐均有签章。三、柏莱公司所举证据确实充分。2009年7月6日,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转让公司股权时,柏莱公司仅有出让土地一块,支付土地出让金400余万元,公司注册资金21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为1600余万元,对剩余注册资金1200万元的去向,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既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不能说明清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柏莱公司一审期间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柏莱公司的上诉,张颖斐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柏莱公司提出的2006年12月25日、12月28日、12月30日分别支付至姜晓东账户的106.3万元、110.88万元以及82.41万元系张颖斐、姜晓东共同抽逃出资的主张没有采纳是正确的。二、柏莱公司主张张颖斐应对上述款项支付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三、柏莱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姜晓东与张颖斐存在共同抽逃出资的行为。姜晓东也不是柏莱公司的股东,不具有抽逃出资的可能。四、柏莱公司主张的各股东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张颖斐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张颖斐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柏莱服饰公司三位原股东于2008年6月10日与孙福财签订。柏莱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孙福财所称的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之需而提供的文本,在三位原股东签名后取走且落款日为2009年7月6日,由孙德静代表的香港时运公司作为股权转让方。虽然双方提供的股权转让书受让方不同,但在张松伟、郑洁、张绍平提交的证据3柏莱服饰公司财务报表附注(2009年度)中,孙福财与孙德静同时出现在“年末其他应收款主要债务人情况”表格中。除此之外,该证据3中的2010年度、2011年度信泰联合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以及柏莱服饰公司财务报表附注(2010年度)中应收款均有孙福财出现。证明了柏莱公司破产之前一直由孙福财实际控制,这在洞头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查清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应依职权追加孙福财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二、一审法院认定柏莱公司转入张颖斐账户的三笔分别为139.08万元、250万元、50万元的款项为抽逃出资的事实错误。1、活期账户交易历史查询显示,2006年12月11日当天有多条交易记录,其中一条是现金支取139.08万元,而另一条是现金存入139.08万元,且支取在前存入在后。当日,张颖斐因采购针织内衣需要采用现金支票方式支取现金139.08万元,但后来取消了采购计划,又于当日将现金如数存入公司账户。柏莱公司提交的现金支票及银行的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审批表反映的仅仅是其中部分事实,同时现金支票以及登记审批表上现金用途栏注明的“购针织内衣”也印证了张颖斐的陈述。再者,以柏莱服饰公司为收款人的现金支票,由当时作为董事长的张颖斐提现,然后向供货商采购是公司经营的正常行为。2、在活期账户交易历史查询上,2007年2月13日同时存在两条交易记录,一条是存入412万元,一条是支取250万元。针对支取的250万元,柏莱公司已提交了现金支票及银行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审批表来证明,张颖斐也确实收到了该款项。根据柏莱公司提供的温州诚达联合会计事务所验资报告记载,“截止2007年2月9日,公司股东本次出资连同以前出资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2007年2月9日已经出资。在完成出资后,张颖斐作为当时公司的董事长出于运营需要筹集412万元资金存入公司账户,又因购货需要支取250万元,资金来源并非公司资本。3、往来户明细表上,2007年5月21日存入50万元,次日支取50万元。这同样是在验资完成后发生,也不属于抽逃出资行为。4、由于柏莱公司企业管理体制不完善,张颖斐缺乏企业管理知识,再加上张颖斐为了众所周知的财务规避原因采用个人账户与客户、供货商直接交易,以及公司原股东已经100%转让股权,原公司财务账册凭证等交由受让方长达六年之久,张颖斐也不可能再举出相关证据。三、本案不属于承债式企业收购,原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在公司股权转让时已剥离。张颖斐收到上述三笔款项即使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用于公司经营,退一万步讲也只是欠公司的款项,对公司而言是应收款。本案无论孙福财或香港时运公司在以原公司股权转让方式收购原公司时,并不承受原公司的债权债务。即在原公司股权转让的时候目标公司的债权并未转至新股东经营的公司,即不在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财产范围。在柏莱公司提供的柏莱服饰公司财务报表附注2009年度的“其他应收款主要债务人情况”中未有张颖斐的该应收款,可以证明该应收款并未转让。包括张颖斐在内的原股东与孙福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对价只有1250万元,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对应的目标公司的资产仅为土地使用权和公司外壳,并无目标公司债权或债务。换言之,公司在新旧主体变更过程中已放弃了该债权,现早已过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法律条款中“公司债权人”以及“股东”应作限缩解释。公司债权人请求承担清偿责任的股东应该是债权形成时的股东而不是任何时期的股东。本案中,张颖斐的股权已经转至新股东名下,破产债权均是新股东经营所产生,故这些债权人无权要求张颖斐承担清偿责任。本案中,柏莱服饰公司变更为柏莱公司并不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股东抽逃出资只能向外商追缴。五、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柏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福财与柏莱公司工商登记股东香港时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柏莱公司的诉讼请求。
针对张颖斐的上诉,柏莱公司辩称:一、本案无需追加孙福财和香港时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1、本案存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柏莱公司原股东在与孙福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与香港时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孙福财代表香港时运公司向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符合隐名代理的规定。2、本案所涉追收抽逃出资的事实均发生在柏莱公司原股东转让股份之前,故孙福财是否柏莱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本案无关。3、柏莱公司原股东如果认为其抽逃出资应由孙福财支付,可以在补缴出资后另行向孙福财主张。二、关于支付至张颖斐账户的三笔款项是否属于抽逃出资的问题。1、关于139.08万元问题。2006年12月11日,张颖斐以购针织内衣名义从公司支取139.08万元,同日又存入139.08万元作为投资款而非还款,一审法院也将该笔存入的139.08万元计入张颖斐的出资。同一笔款项不能既作为出资又作为还款。2、关于250万元的问题。张颖斐辩称其于2007年2月13日通过一些途径筹集412万元存入公司账户,当日又因购货需要支取250万元,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单当日存入的412万元是同户名而非张颖斐,实际为柏莱公司不同账户间的转账。3、关于50万元的问题。2007年5月21日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是有一笔50万元款项进账,但交易对方是温州骑士佳音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而非张颖斐。4、上述三笔款项均系张颖斐直接支取并不存在交易第三方。张颖斐虽然辩称存在交易相对方,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三、股权转让后张颖斐缴纳出资的义务并不能免除。
张松伟、张绍平、郑洁、阿尔凡公司二审辩称:一、张松伟、张绍平并不存在抽逃出资3399481.80元的事实(柏莱公司主张张松伟抽逃出资150万元、张绍平抽逃出资1899481.80元)。1、柏莱公司有做外贸服装生意。事先柏莱公司因购服装而支付150万元货款给郑洁,购买原材料支付1899481.80元给阿尔凡公司,这两笔汇款只能说明该公司的资金流向。前述货物出卖后,被上诉人于2010年8月3日通过阿尔凡公司账户汇款400万元回笼给柏莱公司。2、这两笔款项均是柏莱公司汇给郑洁、阿尔凡公司,而不是张松伟、张绍平。3、柏莱公司与郑洁、阿尔凡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均有合同、发票、汇款凭证。股权转让后,柏莱公司原股东将公司的所有合同、发票、汇款凭证、账册移交给公司。现相关证据材料应由柏莱公司提交。4、柏莱公司属于法人独资公司,管理混乱。二、张松伟、张绍平根本不存在对张颖斐392万元款项负连带返还责任。三、柏莱公司2011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信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充分证明柏莱公司没有亏损。四、柏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孙福财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和虚假破产犯罪。
姜晓东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法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2007年5月9日,柏莱服饰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账户向温州市骑士佳音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当时公司账户余额为190774.71元。2007年5月21日温州市骑士佳音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汇入柏莱服饰公司中信银行账户50万元,当时公司账户余额为690774.71元。2007年5月22日张颖斐从柏莱服饰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支取50万元。柏莱服饰公司广发银行账户记载的2007年2月13日汇入款项412万元实际是由该公司中信银行账户同户名转入。而根据柏莱服饰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明细及相关凭证反映,2007年2月13日该账户余额8680850.02元,主要系由2007年2月2日张松伟作为资本金现金存入335万元和2007年2月9日从朱和东账户以还款名义转入400万元构成。郑洁是张松伟的妻子,张颖斐与姜晓东的户籍所在地同为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山根南路27号,张绍平与郑秀燕的户籍所在地同为温州市瓯海区丽岙街道岩中路2号。郑洁、郑秀燕从2002年起就是阿尔凡公司的股东,郑洁为阿尔凡公司董事长,郑秀燕为该公司副董事长。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需要追加孙福财和香港时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司有权要求受让股东对出让股东出让股权之前的瑕疵出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承担连带责任,但在公司没有就此提出主张的时候,并没有将受让股东列为共同诉讼当事人的规定,故张颖斐提出法院没有将股权受让人孙福财或香港时运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属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张颖斐2006年12月11日、2007年2月13日、2007年5月22日从柏莱公司支取1390800元、250万元和50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争议。柏莱公司主张其原股东张颖斐在股权转让之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柏莱公司提供的相关财务凭证及账目可以证实张颖斐在柏莱服饰公司成立后至2009年7月股权转让前共向公司注入包括应缴纳220万美元(7511106.50元)出资款在内的款项合计为7981400元(已剔除2006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9日期间投入并被退回的4870800元款项的收入和支出),超出章程规定的应缴纳出资款数额为470293.50元的事实以及期间张颖斐分别于2006年12月11日、2007年2月13日和2007年5月22日以购针织内衣、货款(服装、皮件)等名义从公司账户支取1390800元、250万元、50万元,共计439.08万元款项的事实。上述证据属于足以令人对张颖斐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经二审进一步查明,2006年12月11日,张颖斐确实存在以购服装、皮件名义先从公司账户支取1390800元之后再以投资款名义汇入公司账户1390800元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在计算张颖斐汇入公司的总出资款时已将张颖斐汇入公司的该笔1390800元投资款计算在内,故张颖斐提出2006年12月11日汇入公司的1390800元投资款就是归还同日支取的1390800元购货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2007年5月9日,柏莱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账户向温州市骑士佳音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当时公司账户余额为190774.71元,2007年5月21日温州市骑士佳音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汇入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50万元,当时公司账户余额为690774.71元,2007年5月22日张颖斐从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支取50万元。根据上述事实,二审法院认为张颖斐提出的2007年5月21日其向柏莱公司账户存入50万元并于次日支取50万元,即支取的50万元实际是其所筹集资金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柏莱公司广发银行账户记载的2007年2月13日汇入的412万元实际是由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同户名转入,且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上当时的存款余额主要来源于2007年2月2日张松伟作为资本金现金存入的335万元和2007年2月9日从朱和东个人账户以还款名义转入的400万元,并非张颖斐所筹集。张颖斐提出系其通过一些途径筹集412万元资金存入公司账户,当日又支取250万元的主张也与事实不符。张颖斐作为柏莱服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虽然否认抽逃出资事实,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交易事实,结合柏莱公司管理人在接管公司财务账册后没有发现张颖斐所主张交易的合同、发票、入库单、账面存货记录以及二审查明的柏莱服饰公司账户上述争议款项的收支事实等,二审法院确信柏莱公司主张的张颖斐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认定张颖斐从公司支取上述三笔款项(扣除多余出资款部分)属于抽逃出资。一审法院将张颖斐从公司支取的上述三笔款项(439.08万元)扣减其多出资款项(470293.50元)后的数额(3920506.50元)认定为系张颖斐抽逃出资的金额并无不当。(三)关于张颖斐以预付针织内衣货款名义三次从柏莱公司合计转出2995900元给姜晓东的行为、张松伟2007年2月16日从柏莱公司以购货款名义开具150万元现金支票给郑洁的行为以及张绍平以购材料名义从柏莱公司转出1899481.80元给阿尔凡公司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的争议。柏莱服饰公司的原股东张颖斐、张松伟以及张绍平以购货等名义将公司上述款项分别转至关系人或配偶或关系人投资设立的公司名下,在柏莱公司管理人提供上述足以令人对转款原因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的情况下,转款实施人与款项收取人虽然辩称转款系因系正常交而产生,但对其主张的正常交易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结合柏莱公司管理人在接管公司财务账册后没有发现任何相关交易的合同、发票、入库单、账面存货记录等事实,二审法院确信柏莱公司主张的张颖斐以预付针织内衣货款名义三次从公司合计转出2995900元给姜晓东的行为、张松伟2007年2月16日从柏莱公司以购货款名义开具150万元现金支票给郑洁的行为以及张绍平以购材料名义从柏莱公司转出1899481.80元给阿尔凡公司的行为,属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认定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的上述行为构成抽逃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二审法院对柏莱公司提出的张颖斐返还出资2995900元及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姜晓东并非柏莱服饰公司的股东,柏莱公司要求姜晓东共同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张松伟、郑洁、张绍平于2010年8月3日已通过阿尔凡公司账户汇款给柏莱公司400万元,阿尔凡公司对上述事实出具书面证明,同时柏莱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对阿尔凡公司存在其他400万元应收债权,故二审法院认定张松伟、张绍平抽逃的3399481.80元出资已经在事后返还给柏莱公司,柏莱公司关于张松伟、张绍平、郑洁、阿尔凡公司共同承担抽逃出资返还责任的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张松伟、张绍平是否应对张颖斐的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柏莱公司主张柏莱服饰公司原股东张松伟、张绍平对原股东张颖斐上述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松伟、张绍平对张颖斐抽逃出资存在协助的行为或事实,二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浙江省洞头县人民法院(2014)温洞商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张颖斐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柏莱公司抽逃出资3920506.5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以1390800元从2006年12月11日起、2029706.50元从2007年2月13日起、50万元从2007年5月22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为止);二、撤销浙江省洞头县人民法院(2014)温洞商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三、张颖斐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返还柏莱公司抽逃出资29959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以1063000元从2006年12月25日起、1108800元从2006年12月28日起、824100元从2006年12月30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为止);四、驳回柏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3891元,保全费5000元,由柏莱公司负担39234元,张颖斐负担796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92元,由柏莱公司负担37584元,张颖斐负担76308元。
张颖斐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审理程序违法,导致了原审判决结果错误,应依法发回重审。(二)一、二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不实,所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颖斐抽逃出资的事实。(三)本案系因柏莱公司的受让人孙福财及柏莱公司现法定代表人陶琼照涉嫌挪用资金罪和虚假破产罪而提起的虚假诉讼。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二、将本案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柏莱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柏莱公司负担。
柏莱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姜晓东依法应与张颖斐共同返还柏莱公司抽逃出资本金2995900元及利息。(二)张松伟应当与郑洁共同返还抽逃出资本金150万元及利息。(三)张绍平依法应当与阿尔凡公司共同返还抽逃出资本金1899481.80元及利息。(四)柏莱公司收到阿尔法公司的400万元款项,依法不得抵销张松伟、张绍平对柏莱公司的抽逃出资义务。(五)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依法应当互负连带还款责任。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第四项;2.依法改判姜晓东与张颖斐共同承担二审判决第三项款项;3.依法改判张松伟、郑洁向柏莱公司返还抽逃出资本金15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7年2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4.依法改判张绍平、阿尔凡公司共同向柏莱公司返还抽逃出资本金1899481.8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本金1571875.50从2005年12月21日起、本金327606.30元从2005年1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5.依法改判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对上述第2项、第3项、第4项款项及二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要求张颖斐承担责任的款项互负连带偿还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张颖斐、姜晓东、张松伟、张绍平、郑洁、阿尔凡公司负担。
张松伟、张绍平、阿尔凡公司、郑洁针对张颖斐、柏莱公司的再审申请答辩称:(一)张松伟确实不存在抽逃出资3399481.80元的事实,亦不存在抵销的问题。(二)张松伟、张绍平对张颖斐的款项不负有连带偿还责任,以及阿尔凡和郑洁不存在返还款项的责任。(三)柏莱公司及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福财涉嫌虚假破产罪。(四)张松伟根本没有要求柏莱公司汇款400万元给张荣武。案涉400万元系阿尔凡公司代柏莱公司收取的货款,其中3399481.80元为成本,600518.20元是利润。综上,请求驳回柏莱公司的再审申请。
再审中,张颖斐提供了五组证据材料:证据1,洞头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二份,案号分别为(2013)温洞商破字第1-1号、1-2号。拟证明柏莱公司在其破产当中提交的相关财务账册报表等材料不完整、不齐全,有虚假嫌疑,柏莱公司对有利于张颖斐的相关证据未提交给原审法院。证据2,2007年2月9日中信银行进账单回单一份,拟证明张颖斐当日归还了柏莱公司400万元款项,不存在涉嫌抽逃出资的事实。证据3,2008年12月31日收据的记账联,拟证明张颖斐当日归还柏莱公司2509609.08元,不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证据4,2007年的2月9日的记账凭证与收款收据的记账联,拟证明当日姜晓东归还柏莱公司2995900元,柏莱公司将款项汇给姜晓东之后,姜晓东如数归还柏莱公司。证据5,2010年8月4日的工商银行的记账单,拟证明柏莱公司向陶琼照汇款400万元的事实,该笔无理由汇款至今未收回,柏莱公司在张颖斐转让后财务管理混乱及自身抽逃资金。柏莱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柏莱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真实完整,且其破产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其系虚假破产。证据2,进账单本身是真实的,但付款人的全称系经过修改的,中信银行留底存档里面是没有张颖斐的名字的,具体二审卷宗可以看到。证据3、证据4,只是收据,没有银行汇款记录,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5,管理人与柏莱公司是两个概念,柏莱公司账不规范,不是本案审理范围。
张松伟、张绍平、阿尔凡公司、郑洁质证认为:证据1,对第一份民事裁定书三性无异议。对第二份民事裁定书三性有异议,柏莱公司不具备破产条件,宣告其破产不合法。证据2-5,均为复印件,真实性由合议庭审查。
本院认为,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亦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2,不是新证据,且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因为根据温州银行出具的朱和东账户的存款明细单,该400万元款项是从朱和东账户直接汇入柏莱公司账户的,而非张颖斐汇入。证据3,不是新证据,且仅仅有收据,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4,不是新证据,且仅仅有收据、记账凭证,没有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5,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
除二审对张松伟、郑洁、张绍平2010年8月3日通过阿尔凡公司账户汇款给柏莱公司4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外,本院对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查明的事实结合争议焦点的分析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颖斐是否构成抽逃出资3920506.50元;二、张颖斐是否另构成抽逃出资2995900元及姜晓东是否应与张颖斐对该2995900元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张松伟是否构成抽逃出资150万元及郑洁是否应与张松伟对该150万元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张绍平是否构成抽逃出资1899481.80元及阿尔凡公司是否应与张绍平对该1899481.80元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三、对上述款项,如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构成抽逃出资,该三人是否应负连带还款责任。
争议焦点一。张颖斐在柏莱服饰公司成立后至股权转让前共向公司出资7981400元,超出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缴纳出资款项数额470293.50元。张颖斐分别于2006年12月11日、2007年2月13日和2007年5月22日以购针织内衣、货款(服装、皮件)等名义从公司账户支取1390800元、250万元、50万元,共计439.08万元,上述事实根据柏莱公司提供的相关财务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对张颖斐2006年12月11日汇入柏莱公司的1390800元款项,因该款项已计算在其出资款项数额内,故该款项不能作为其同日支取的1390800元购货款的还款。对张颖斐2007年5月22日从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支取的50万元款项,因该50万元款项实际系温州市骑士佳音汽车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21日汇入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故张颖斐主张该50万元款项系其同日汇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张颖斐2007年2月13日从柏莱公司广发银行账户支取的250万元款项,该广发银行账户2007年2月13日汇入的412万元实际是由柏莱公司中信银行账户转入,且该中信银行当时账户中的存款余额主要来源于2007年2月2日张松伟作为资本金现金存入的335万元和2007年2月9日从朱和东个人账户以还款名义转入的400万元,故张颖斐主张该250万元款项系其筹集,同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述事实有款项转入前后的账户余额及转账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再审中,张颖斐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推翻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据此,二审法院以张颖斐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交易事实,柏莱公司管理人在接管公司财务账册后没有发现与张颖斐主张相关的交易合同、发票、入库单、账面存货记录等,认定张颖斐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3920506.5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有相应依据。同时,对于张颖斐提出的重新审计申请、证据调查申请,因上述申请事项均与本案无关,故对其上述申请事项均不予准许。
争议焦点二。张松伟、张绍平辩称其未抽逃出资,并称柏莱公司为履行其与外方客户签订的外贸销售合同,汇给郑洁150万元向其购买服装,汇给阿尔凡公司1899481.80元向其购买原材料。外方货款收回后,张松伟、张绍平、阿尔凡公司、郑洁于2010年8月3日通过阿尔凡公司的账户汇款400万元给柏莱公司(包括盈利)。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张松伟、张绍平对其主张的柏莱公司与郑洁、柏莱公司与阿尔凡公司、柏莱公司与外方客户分别存在的货物买卖关系,并未提供交易合同文本、货物交付凭证、结算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其次,柏莱公司对收到的上述400万元款项,在其原始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款项性质为“周转款”,而非货款;再次,正常情况下,作为买方的外方客户向作为卖方的柏莱公司付款,一般会直接汇入柏莱公司账户,而不会汇给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其他人,在张松伟、张绍平、阿尔凡公司、郑洁未提供证据证明柏莱公司委托其作为受托人代收货款及柏莱公司指示外方客户将款项支付给其受托人的情况下,张松伟、张绍平的上述抗辩,不能成立。据此,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以购货等名义分别将柏莱公司2995900元、150万元、1899481.80元转至关系人或配偶或关系人投资设立的公司名下,且均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系正常交易,二审结合柏莱公司管理人在接管公司财务账册后没有发现任何相关交易的合同、发票、入库单、账面存货记录等事实,认定上述三人的行为系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或利用关联交易将其出资转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构成抽逃出资,有相应依据。对张松伟、张绍平抽逃出资部分,在张松伟、张绍平的上述抗辩不能成立的情况下,二审以张松伟、郑洁、张绍平于2010年8月3日已通过阿尔凡公司账户汇款给柏莱公司400万元,柏莱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对阿尔凡公司存在其他400万元应收债权为由,认定张松伟、张绍平抽逃的3399481.80元出资已经在事后返还给柏莱公司,有所不当,应予纠正。故对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抽逃的上述出资及利息,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应当返还给柏莱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七条“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提起诉讼,主张被隐匿、转移财产的实际占有人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主张债务人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无效并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该规定中虚构债务的主体为债务人即被宣告破产公司,而姜晓东、郑洁、阿尔凡公司并非债务人,故柏莱公司据此要求姜晓东、郑洁、阿尔凡公司返还基于虚构债务而占有的柏莱公司财产并共同承担抽逃出资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本案柏莱公司设立时原三发起人股东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的出资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并非未履或者未全面履行,故柏莱公司据此请求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对各自抽逃出资的返还负连带责任,不能成立。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一款“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柏莱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颖斐、张松伟、张绍平相互之间对他人抽逃出资部分存在协助的行为或事实,故二审对柏莱公司的相关主张未予支持,有相应依据。
综上,柏莱公司的再审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张颖斐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商终字第282号民事判决和洞头县人民法院(2014)温洞商初字第96号民事判决;
二、张颖斐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抽逃出资款6916406.5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以1390800元自2006年12月11日起、2029706.50元自2007年2月13日起、50万元自2007年5月22日起、1063000元自2006年12月25日起、1108800元自2006年12月28日起、824100元自2006年12月30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三、张松伟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抽逃出资款1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07年2月1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四、张绍平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抽逃出资款1899481.8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以1571875.50元自2005年12月21日起、327606.30元自2005年12月2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
五、驳回温州柏莱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3695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颖斐负担59426元,张松伟负担13304元,张绍平负担159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3695元,由张颖斐负担56076元,张松伟负担12554元,张绍平负担1506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光洁
代理审判员 方小欧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曼菁
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月新、陈继泉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月新、陈继泉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浙06民终25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1461500012。
法定代表人:何之骥。
诉讼代表人: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组织机构代码47134676-1。
主要负责人:周利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蔚明,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月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继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光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星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光兴。
上述七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钧,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七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国,浙江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火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会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建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浩明。
上述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倩,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良。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铭君。
上诉人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月新、陈继泉、陈国民、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余光兴、夏火明、高会兴、潘建新、乐浩明、周建新、周建良、李铭君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4民初3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德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企业改制问题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系由原上虞四建以0资产改制,根据相关文件进行设立登记,而非变更形成。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虞四建注册资本3331万元系虚增固定资产及实收资本形成。周月新等人支付的80万元系为上虞四建清偿债务,而非为上诉人清偿债务。上诉人以0资产改制,必然承接上虞四建资产和债务,不能据此判断为企业延续。企业改制是所有制改变,是企业资产买卖,不是公司股权转让。即使沥海镇政府文件称委派工作人员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注册资金连续等,不能与国务院政策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相悖,不能将上述做法作为判断企业主体延续的依据。2、在验资后,上诉人帐户验资款被出资人抽逃,因上诉人帐上无具体交易信息,相关资金流转不能认定为交易所需。所作“其他应收科目-各项目部”1417.32万元的假帐,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上诉人是否完成整体破产审计,不影响司法鉴定结论的正确性。3、虚构债权债务将出资转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且损害公司利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
被上诉人周月新、陈继泉、陈国民、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余光兴二审辩称:1、上虞四建属负资产,相应负债由改制后的上诉人自身经营弥补,故企业资产尚存。2、资产转让行为本身说明新老企业存在承继关系,0资产转让不能隔断承继关系。改制前后企业,在建筑资质、人员、业务各方面存在延续性。3、办理新设登记是政策性要求,但新老企业在工商档案中仍属同户,表明实质系变更登记。4、本案系企业转制性质,相关手续均由政府办理,七被上诉人没有出资义务。5、最高法院企业改制司法解释不适用本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夏火明、高会兴、潘建新、乐浩明二审辩称:认可前列七被上诉人意见。四被上诉人已支付对价,无须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德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周月新立即补缴出资230.4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230.4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陈继泉立即补缴出资135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135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陈国民立即补缴出资196.65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196.65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被告金光明立即补缴出资172.47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172.47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5.被告余永根立即补缴出资355.6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355.6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6.被告朱星火立即补缴出资175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7.被告余光兴立即补缴出资152.2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152.2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8.被告周月新、陈继泉、陈国民、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余光兴对上述各被告的补缴出资责任(以总补缴出资额为1417.32万元为限)互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9.被告夏火明对被告周月新的上述责任在39468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夏火明对被告金光明的上述责任在10000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05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0.被告周建新对被告周月新的上述责任在18876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周建新对被告陈国民的上述责任在16224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05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1.被告高会兴对被告周月新的上述责任在5616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高会兴对被告金光明的上述责任在8892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高会兴对被告余永根的上述责任在88920元及其利息损失(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05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2.被告潘建新对被告周月新的上述责任在18291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潘建新对被告余光兴的上述责任在42754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05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3.被告乐浩明对被告余光兴的上述责任在1479246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05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4.被告周建良对被告金光明的上述责任在153578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周建良对被告余永根的上述责任在51252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12年7月3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5.被告李铭君对被告陈国民的上述责任在180426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利息的计算分别以各自的基数从2013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补缴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16.本案受理费及保全费用由上述十四名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第8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被告陈国民立即补缴出资196.65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按以196.65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被告金光明立即补缴出资172.47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按以172.47万元为基数,自2000年12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中被告潘建新对被告余光兴的上述责任在51090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第13项诉讼请求中被告乐浩明对被告余光兴的上述责任在1767669元及其利息损失限额内负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上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而来,成立于2000年12月27日,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前的上虞四建注册资金为3331万元。2000年4月29日,上虞同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虞同评(2000)第7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上虞四建剔除待处理资产损失后的净资产为-3259663.13元。2000年8月18日,上虞市沥海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与周月新等七人签订《无形资产转让协议》,上虞市沥海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将原上虞四建(建筑二级资质)无形资产经评估值为80万元有偿转让给周月新等七人。原上虞四建所承担的未竣工项目业务给周月新等七人管理。2000年11月18日,上虞四建文件显示:沥海镇人民政府委派主管工业镇长吕水荣同志和镇工办工作人员俞金玉同志一起主导办理上虞四建企业改制的工商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变更、注册资金连续等手续。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德盛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股东为陈国民、陈继泉、金光明、余光兴、余永根、朱星火、周月新。其中,周月新出资额480万元,陈国民、陈继泉、金光明、余光兴、余永根、朱星火的出资额均为420万元。2003年9月8日,德盛公司注册资本金从3000万元变更为6225万元。2004年3月5日,股东变更为余永根、余光兴、金光明、陈国民、周月新。2005年12月20日,股东变更为高会兴、潘建新、乐浩明、余永根、金光明、周建新、朱星火、陈国民、夏火明、周月新。2007年4月17日,德盛公司注册资本金从6225万元变更为7725万元。2012年7月6日,德盛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周建新、陈国民、周月新、周建良。2012年7月20日,股东变更为陈国平、余纪明、俞国龙、周瑞宝、周建新、陈国民、周月新、周建良。2013年6月14日,股东变更为周建新、周月新、周建良、李铭君。
2000年12月23日,上虞同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虞同会验(2000)字第535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00年12月22日止,德盛公司已收到其股东投入的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都是实收资本。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为3000万元,其中货币资金1417.32万元,实物资产1582.68万元。验资报告附件投入资本明细表载明,股东周月新货币资金为230.40万元,陈继泉货币资金为135万元,金光明货币资金为172.47万元,朱星火货币资金为175万元,余光兴货币资金为152.20万元,余永根货币资金为355.60万元,陈国民货币资金为196.65万元。
2000年12月14日,银行凭据显示从德盛公司57220110032118账号转账至金光明135万元,余光兴105万元,陈继泉135万元,转账支票票面记载“转款”,汇款至朱星火175万元,汇票委托书存根记载汇款用途“材料款”。2000年12月15日,汇款至上海锦丽斯房地产有限公司100万元,汇票委托书存根记载汇款用途“材料款”。2000年12月18日,现金支票转出103.6万元,现金支票票面记载用途“购设备”,现金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俞金玉”、用途“归还借款”。2000年12月22日,分两次转账至陈继泉400万元及186万元,400万元的转账支票票面记载“购设备”,186万元的转账支票票面及存根均记载“转款”。2000年12月25日,分三次现金支票转出20万元、40万元及227200元。现金支票票面记载用途“购设备”,现金支票存根记载收款人“俞”、用途“归还借款”、“还款”。2001年4月30日,德盛公司记账凭证记载1422.32万元款项“借: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沥海信用社”。截至2014年5月31日,德盛公司账目中“其他应收款-各项目部”余额为1417.32万元。
同时查明,2003年7月30日,余永根分别与周月新、陈国民、金光明、陈继泉、朱星火、余光兴签订股金转让协议,将其股金转让给周月新、陈国民、金光明、陈继泉、朱星火、余光兴。2004年2月20日,陈继泉、朱星火分别与周月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陈继泉转让给周月新现金股本金135万元,朱星火转让给周月新现金股本金175万元。2005年12月5日,德盛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周月新将货币出资1173510元分别转让给周建新1887某某元、朱星火351000元、高会兴56160元、夏火明394680元、潘建新1829某某元。同意陈国民转让给周建新货币出资162240元,金光明分别转让给高会兴货币出资88920元及夏火明10万元,余永根转让给高会兴货币出资88920元,余光兴分别转让给潘建新货币出资51090元及乐浩明1821413元。2005年12月12日,上述股东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2012年7月3日,德盛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夏火明、高会兴、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潘建新、乐浩明将其持有的德盛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周建良,并分别与周建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7月13日,德盛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周建良将其持有的德盛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俞国龙、余纪明、陈国平及周瑞宝,并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5月30日,陈国平、余纪明、俞国龙、周瑞宝、陈国民将各自持有的德盛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李铭君,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另查明,2003年9月8日,德盛公司的名称从上虞市德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5月15日,该院依法受理德盛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8年4月28日,绍兴通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绍通大专审字【2018】0074号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1、周月新、陈继泉、陈国民、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余光兴七人在德盛集团认缴出资3000万元的事实存在;2、周月新、陈继泉、陈国民、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余光兴货币出资的1417.32万元,均于缴款当日转出;财务资料中应收款项的挂账也体现该出资既没有在公司使用,也没有回流公司,未提供使用资金的证据,没有相关合同、利息,没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上述情况形成抽资的事实。本次鉴证咨询服务费及审计费共975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周月新、陈继泉、陈国民、金光明、余永根、朱星火、余光兴等七被告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理由如下:
第一,绍通大专审字【2018】0074号司法鉴定报告虽然认为七被告的货币出资1417.32万元于缴款当日转出,形成抽资的事实,但根据德盛公司57220110032118银行账号资金进出明细及相关银行交易凭据,2000年12月15日汇款转出的100万元,收款人为上海锦丽斯房地产有限公司,汇款用途记载为“材料款”。2000年12月18日以现金支票转出的103.6万元,收款人为“俞金玉”,现金支票票面与存根记载的用途分别为“购设备”及“归还借款”。2000年12月25日以现金支票转出的827200元,收款人为“俞”,现金支票票面与存根记载的用途分别为“购设备”及“归还借款、还款”。上述几笔转款收款人均不是七被告,且票面记载的转款用途为“材料款”或“购设备”,而现金支票存根记载为“归还借款”或“还款”,转款用途记载并不一致。此外,俞金玉在调查笔录里陈述自己用现金支票取款后将款项归还给时任沥海信用社主任戴苗祥,因验资的部分资金系向沥海信用社及戴苗祥借款。但俞金玉的上述陈述亦无相应证据加以证实。
第二,原告向该院申请“对2000年12月七被告以注册资本3000万元发起设立德盛公司时,各被告的认缴出资、出资(虚假出资)、验资以及通过其他应收科目-各项目部名义挂账抽逃出资”的事实进行专项审计,后该院依法委托绍兴通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七被告的认缴出资、实缴出资、验资及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情形进行审计。审计机构依据2000年德盛公司57220110032118账户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资金流水记录、相关银行凭据,德盛公司其他应收款-各项目部的明细账、相关会计凭证,出具绍通大专审字【2018】0074号司法鉴定报告,认为七被告存在抽资的事实。但上述审计资料仅反映了德盛公司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这一时间段内的银行账户交易,且部分款项转出凭据票面与存根记载的用途并不一致,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验资后的资金去向及用途并不明确。德盛公司截至2014年5月31日其他应收款-各项目部期末余额1417.32万元的明细账系德盛公司的内部记账,而德盛公司整体的破产审计至今并未完成,单凭内部财务记账中应收款项的挂账并不能必然得出出资未在公司使用或回流公司的结论。
第三,认定股东抽逃出资,除了符合“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列举的四项情形之一的形式要件,还应符合损害公司权益的实质要件。若仅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不符合实质要件,也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抽逃出资。该院经向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德盛公司与上虞四建的工商登记为同一户,德盛公司系上虞四建改制而来,改制前的上虞四建注册资金为3331万元。该院经向沥海镇人民政府调查,2000年8月18日,上虞市沥海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将原上虞四建(建筑二级资质)无形资产经评估值为80万元有偿转让给周月新等七人,并约定原上虞四建所承担的未竣工项目业务也给周月新等七人管理。沥海镇人民政府明确已收到上虞四建转制款共80万元,并提供了现金缴款单及收费统一票据。而2000年11月18日的上虞四建文件亦显示:沥海镇人民政府委派主管工业镇长吕水荣同志和镇工办工作人员俞金玉同志一起主导办理上虞四建企业改制的工商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变更、注册资金连续等手续。由此可见,上虞四建改制为德盛公司过程中,周月新等七股东向原上虞四建主管单位购买了建筑二级资质的无形资产,并继续管理上虞四建承担的未竣工项目。审计资料中2000年12月14日金额为50100元的现金缴款单显示收款单位为德盛公司,款项来源为工程款,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德盛公司成立过程中已在收取上虞四建在建项目的工程款。结合周月新等七股东与原上虞四建项目部的身份关系、建筑二级资质无形资产的转让、沥海镇政府工作人员主导办理注册资金连续手续、上虞四建未竣工项目延续等客观事实,本案在验资款项转出的实际用途与去向并不明确且德盛公司整体的破产审计亦未完成的情形下,审计报告所认定的形成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否实际损害德盛公司的权益亦不确定。
综上所述,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周月新等七被告抽逃出资,对原告主张周月新等七被告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原告主张其他受让股东承担相应连带清偿责任,亦不予支持。被告周建新、周建良、李铭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作缺席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839元,鉴定费用9750元,由原告负担。
当事人在二审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其一,相关司法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报告并未考虑上诉人系改制企业性质,且未就可能存在的上诉人及股东代偿原企业债务、弥补原企业亏损及投入列入审计范畴,同时上诉人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属于司法判断权,鉴定机构无权进行评判。其二,因上诉人系原集体企业上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政策性改制形成,周月新等七人以零资产受让原企业,并对价支付了原企业相应无形资产,当地政府根据上级要求主导推动并办理了工商执照、资质证书变更、注册资金连续等改制工作,现两者工商登记仍属一户,且原企业注册资本金经工商登记为3331万元。同时,在改制前后,两企业存在人员、资质、未竣工项目管理等延续性。通过上述方式将原集体企业整体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虽上诉人形式上是按设立登记要求提交文件,但并非纯粹的新设有限责任公司,而是企业公司制改造性质,具有政策性特点。本案部分出资款去向并不确定,即使本案部分股东存在将其他部分出资款转入公司帐户验资后又转出行为,但该行为是否损害公司权益并不确定。据此,本案不能认定为系抽逃出资行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39元,由上诉人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黄叶青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佳婧
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等与浙江××学院不当得利纠纷申请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浙民提字第110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
委托代理人裘××。
委托代理人杜××。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甲。
委托代理人谢××。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学院(原浙江教育学院)。
法定代表人鲁××。
委托代理人郭乙。
委托代理人吴××。
一审被告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
委托代理人裘××。
委托代理人杜××。
申请再审人浙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求是××)、中××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托)与浙江××学院(以下简称外国语××)、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前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7日作出(2008)杭乙一初字第1740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求是××、中××信托不服该一审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4日作出(2010)浙杭民终字第64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求是××、中××信托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于2011年10月13日作出(2011)浙民申字第4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求是××、一审被告通用××的委托代理人裘××、杜××,申请再审人中××信托的委托代理人谢××,被申请人外国语××的委托代理人郭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某:一、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求是学院)前身为浙江求是职业技术学院(筹),于1999年12月6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1999)294号文件批复,由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浙江省委)举办。2002年8月20日,民盟浙江省委与浙江省国某某托投资有限责任甲司(2007年11月20日,名称变更为中××责任公司)、浙江求是科技服务部、孙某某共同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1份,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各方同意合作设立求是××作为浙江求是职业技术学院的全额投资主体,求是××的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其中:浙江省国某某托投资有限责任甲司出资1200万元,占80%;浙江求是科技服务部出资225万元,占15%;孙某某出资75万元,占5%。2002年12月3日,浙江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1份,载明:经其审验,截止2002年11月30日止,求是××(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500万元,全部为货币资金。同日,求是××经工商注册成立。2003年3月28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函(2003)49号文件批复:同意浙江求是职业技术学院(筹)并入浙江科技学院,建立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即本案中的求是学院,同时停止筹建浙江求是职业技术学院;求是学院为浙江科技学院的二级学院,其现有办学规模和层次保持不变,学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校区,相对独立办学,经济独立核算,按民办体制运作。2003年4月28日,求是学院领取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确定举办单位为求是××和浙江科技学院。2005年6月13日,求是学院又领取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2006年8月21日,求是学院董事会向浙江省教育厅提出关于求是学院终止办学及资产转让的请示,该请示表示:经求是学院董事会决议,求是学院终止办学,由省教育厅落实一所高等院校负责接管;由董事会委托有资质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对学院财产进行全面审计,对学院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并根据结果依法处理;建议清算小组由省教育厅、求是××和接管单位三方派员组成,清算工作由求是××组织牵头,董事会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建议资产评估的基准日为2006年8月31日;建议接管单位按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对学院的资产进行评估后的净资产,全额支付给求是××相应的对价,支付时间为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1个月内结清等内容。同日,浙江省教育厅复函求是学院董事会,复函意见为:同意求是学院终止办学,省教育厅安排浙江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教育学院)负责接管,并及时报省政府审批;同意学院董事会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学院的财务进行全面审计,对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并根据结果依法处理。成某某务清算工作小组,具体由求是××牵头,省教育厅、教育学院等派员参加,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6年8月31日;同意教育学院根据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对学院的资产进行评估后的净资产,经省财政厅核准后,在一个月内付清应付的款项。自评估基准日后,求是学院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教育学院享有和承担等内容。同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对省教育厅《关于终止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办学的请?示》作出浙政函(2006)88号批复:同意求是学院终止办学,终止办学后,由省教育厅负责收回办学许可证,由省人事厅负责注销事业法人登记;同意教育学院全面接管求是学院,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法有序地做好人、财、物交接工作,有关教职工的安置、收费标准的确定、学生的生活补贴、基建项目的划转、经费的补助等,按省教育厅提出的方案执行;依法做好财务清算工作,学校终止办学后,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尽快按规定完成清偿、移交工作,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教育厅要加强指导和监督。2006年8月22日,教育学院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上述文件实际接管了求是学院,但求是××未与教育学院办理相关的人、财、物的交接手续,求是××也未牵头组织成某某务清算工作小组。二、求是学院终止办学后,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因刑事侦查需要,在浙江省教育厅提供的求是学院的有关账簿、凭证及相关外部证据等资料的情况下,委托浙江万某司法会计某某事务所、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有限公某对求是××对求是学院的出资情况、求是××注册资本情况、求是××经营的资金来源、使用情况及去向等事项进行了专项审计。根据浙万会专(2006)315号和浙万会审(2007)29号两份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可见:1、求是××对求是学院的账面出资额为1845万元,其中第一笔投资款395万元,系求是学院先?通过银行以往来款的形式划给求是××,同日再由求是××作为投资款划入;第二笔投资款450万元,入账时即账挂“其他应收款-国信求是实业公某”,截止2005年12月31日,求是学院账面仍反映其他应收求是××的款项为541.09万元;第三笔投资款1000万元,是小和山村委会根据其与求是学院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投入求是学院的第一笔项目合作款。小和山村委会共投入求是学院项目合作款1500万元,分别于2004年4月13日和2004年4月28日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划入求是学院未在账面反映的银行隐匿账户1000万元和500万元。求是学院将上述1000万元以转帐支票形式划给求是××,再由求是××作为投资款划入求是学院。从上述求是××出资的资金来源反映,求是××并未对求是学院有实际出资。2、求是××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于2002年12月4日即被转出。3、截止2006年12月31日,求是××账面反映应收求是学院6861145.75元,经审计,通过对求是××经营的资金流入、流出轧抵后,求是××实际应付求是学院13853654.25元,减去应收求是学院茶多酚销售收入114800元,合计应付13738854.25元,与账面应收数差异20800000元,差异原因主要为科目间无依据互转。4、求是××自成立以来,基本没有开展正常的经营业务,2003年至2006年度累计亏损-6352015.49元。2007年2月6日,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向实际控制求是××和求是学院经营、运作的通用××法定代表人高×进行了讯问,高×认可:1、求是××所有股东实际未出资,验资所需1500万元来源于其向他人的借款,在工商登记完毕后,其即将上述款项从求是××帐户转到通用××,最后由通用××还给他人。2、为追加求是××对求是学院的债权,其将小和山村委会的1500万元转入求是学院未建帐的银行帐户,其中1200多万元以往来款名义回到求是学院,余款留在求是××的账户内。三、2007年3月1日,为尽快解决求是学院遗留问题,当时的求是学院、求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某出具授权书1份,委托省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清产核资工作组全权负责求是学院的清产核资等工作。同日,浙江省教育厅成立了求是学院清产核资工作小组,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和教育学院相关人员组成。求是学院清产核资工作小组成立后,委托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有限公某对求是学院截至2006年8月31日止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专项审核。2007年8月27日,该事务所出具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1份,其中审核结果有:1、截止2006年8月31日求是学院的资产总额为100588409.35元,负债总额为137585744.16元。2、截止2006年8月31日,账面反映的资本金为1890万元,其中求是××1845万元,民盟浙江省委员会45万元。求是××出资的资金来源情况仍同前述,即求是××并未对求是学院有实际出资。2008年7月16日,求是学院申请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浙江省教育厅在清算组织负责人意见一栏处签字表示同意,孙某某和浙江科技学院在举办单位意见一栏处签字表示同意,求是学院被注销登记。四、2002年8月16日,浙江省国某某托投资有限责任甲司(2007年11月20日,名称变更为中××责任公司)为乙方,通用××为甲方签订《资金信托合同》1份,其中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委托乙方根据合同要求进行投资运作,乙方受托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资金形成的全部财产为信托财产;甲方指定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受益人;信托期限为十年,自2002年8月31日至2012年8月31日;甲方指定信托财产用于向求是××进行股权投资;如求是××未能成立,乙方在扣除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后,将信托资金返还给甲方,本合同终止;在求是××成立后,乙方按照《中华某某共和国公某法》、公某的章程及甲方的义务行使股东的权利及义务;乙方收取管理手续费,手续费每年按照信托资金的1%收取。双方还就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通用××于2002年11月27日将1200万元信托资金汇给浙江省国某某托投资有限责任甲司,浙江省国某某托投资有限责任甲司将该款用于认缴求是××出资额。求是××成立后,该款又转回给通用××。
2008年11月26日,教育学院向一审法院起诉称:求是××无正当理由和合法依据占用求是学院资金,共计13738854.25元,理应归还。求是学院终止办学后,教育学院根据政府指令全面接管求是学院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教育学院有权要求求是××归还上述款项。中××信托(原浙江省国某某托投资有限责任甲司)根据通用××的委托持有求是××80%的股份,但其实际并未对求是××履行出资义务。通用××作为该80%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在求是××成立以后,利用其实际享有的股东地位,随即抽走公某资本金1500万元。中××信托和通用××的行为严重违反《公某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对求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1、求是××向教育学院归还不当得利款项13738854.25元;2、中××信托和通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求是××、中××信托、通用××三被告承担。在审理过程中,教育学院将上述第2项诉请明确为要求中××信托在其××内承担求是××债务的连带责任,通用××与中××信托共同对求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求是××反诉称:求是学院作为浙江科技学院的二级学院,系民盟浙江省委和求是××投资开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按民办体制运作。根据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05年12月,求是学院净资产达65700162.33元。2006年8月21日,求是学院董事会被迫同意终止办学并进行资产转让。同日,浙江省教育厅复函同意教育学院根据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对求是学院的资产进行评估后的净资产,在一个月内付清应付款项。但此后教育学院既未和求是学院共同进行资产评估,也未向求是学院支付任何财产转让对价,而是单方面接管了求是学院全部财产,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1、教育学院支付求是××因受让求是学院净资产的对价65700162.33元或返还相应财产。2、由教育学院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存在以下三个争议焦点:
一、教育学院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否成立。教育学院就整体收购求是学院虽然未与求是××签订过相关收购协议,但从求是学院董事会给省教育厅的请示以及省教育厅给其的复函和随后的教育学院接管行为看,教育学院与求是××之间存在收购求是学院的法律关系。教育学院继受取得了求是学院后,求是学院此前对外的债权债务应由教育学院享有和承担。根据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的记载,求是学院和求是××之间资金流入、流出轧抵后,求是××应付求是学院人民币13738854.25元。求是学院作为民办学校,在其存续期间,对举办者投入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所有资产由其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因此,求是××作为举办人同样也不得使用、占用求是学院的资产。基于此,求是××本应当严格依法编制会计资料,严格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资金流转,但是求是××不仅未按此履行其义务,反而利用其控制求是学院资金和财务的便利,将求是学院的资产没有正当理由的转至其处,该事实不仅有求是学院和求是××的原始会计资料可以证明,且实际控制上述两家单某某作的通用××的法定代表人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证实了上述事实的客观存在,这种财产利益的变动没有法律原因,可以构成不当得利。求是××对上述资金流转虽未依法编制会计资料但确有法律原因的变动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求是××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任何证据,故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承担返还不当得利款人民币13738854.25元的民事责任。二、关于中××信托和通用××的民事责任乙担问题。中××信托与通用××存在信托关系,即通用××将其所有的资金1200万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中××信托用于求是××的股权投资。但股权资金的来源并不影响中××信托应当按照《中华某某共和国公某法》以及求是××章程的规定依法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求是××的章程,中××信托作为持有80%股权的大股东,有权向求是××委派四名董事,并委派总经理,以便其履行信托职责,行使股东权利。但是,中××信托委派的担任董事的本公某员工周某和姚兵实际只是挂名,并未履行任何管理、经营之职,求是××实际由中××信托委派的另一董事兼总经理的通用××的法定代表人高×在实际经营管理,也就是说中××信托将其对求是××的股东权利义务完全转移给通用××行使。根据《中华某某共和国信某某》的规定,“受?托人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中××信托并未亲自履行信托事务即求是××的股东权利义务,而是将信托事务实际又交给了信托委托人通用××处理,故中××信托与通用××又形成被代理和代理的关系,通用××既是信托委托人又是信托事务的代理人。根据代理的有关法律规定,中××信托作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通用××的代理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通用××违法进行代理活动的,被代理人中××信托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代理行为违法而不表示反对的,由二者互负连带责任。本案中,通用××在求是××成立后的第二天即转走了求是××所有的出资,显然该行为属于违法代理行为,根据前述分析,中××信托和通用××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中××信托被抽逃的出资1200万元实际在通用××处,故该院确定由通用××在1200万元出资范围内对求是××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信托对通用××的上述责任乙担连带责任。三、求是××主张的反诉诉讼请求是否成立。根据前述,教育学院与求是××之间存在收购求是学院的法律关系,虽然求是××实际未对求是学院进行过出资,但该未出资的行为并不使得求是××丧失举办人享有的权利,求是学院可以要求求是××按照约定完成出资行为,而求是××则也有权要求教育学院支付相应的求是学院净资产的对价。但是本案中,根据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06年8月31日止,求是学院严重资不抵债,其资产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负值,故求是××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二条、《中华某某共和国信某某》第三十条、《中华某某共和国公某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实业有限公司向浙江教育学院返还不当得利款13738854.25元,该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付清;二、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抽××内对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中××责任公司对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上述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浙江教育学院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五、驳回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4233元、财产保全某请费5000元,合计109233元,由浙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抽××内对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述所负费用109233元某担连带责任;中××责任公司对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上述所负费某某担连带责任。反诉案件受理费185151元,由浙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求是××、通用××、中××信托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通用××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求是××上诉称:一、求是××作为求是学院的举办人,依法享有对求是学院资产的财产所有权。求是学院终止后,求是学院的财产应归属求是××所有,但本案中教育学院直接地强行接收了求是学院的资产。既然原审认定求是××和被上诉人教育学院之间形成了整体收购法律关系,那么在双方共同对求是学院资产进行整体评估以确定一个公平的交易价格之前,以及被上诉人支付合理对价之前,只可能存在被上诉人占有不当利益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求是××获得不当利益问题,原判支持教育学院不当得利之诉请显然错误。二、原审采纳教育学院单方证据,无理拒绝求是××要求对求是学院资产进行司法评估的要求是不公平的。根据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2月24日出具审计报告,截止2005年12月31日,求是学院有净资产65700162.33元。而被上诉人教育学院提供的两份专项审计报告,系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目的所进行的审计,和资产收购双方以转让财产为目的的资产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行为,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公安机关的审计结论不能作为确定学院资产收购对价的依据。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未支付任何对价无偿占有求是学院资产的客观事实,不仅未支持求是××合理之反诉请求,相反判决求是××再支付1300余某某给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之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教育学院一审诉讼请求,支持其一审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外国语××答辩称:一、求是××认为其是求是学院的举办人,因此享有求是学院的资产所有权,这一观点错误。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第三十六条规定“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因此,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民办学校对其资产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举办人没有任意处置的权利,也不因其举办人身份而当然享有学校财产的所有权。民办学校终止办学以后,首先应当以其资产偿还债务,如有结余,还应当要区分资产的构成及来源,分配给学校资产的原投入者享有。因此,求是××对求是学院的资产并不具有所有权,且求是学院办学系依靠国家支持、学生收费以及求是学院自身向社会举债来筹集经费,求是××没有分文投入,求是学院终止办学以后,求是××对学院资产分配没有任何某某。一审判决认定求是学院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即便求是××为其举办人,也不能侵占、使用学院资产,这一认定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二、被上诉人接管求是学院符合法定程某,且以偿债形式支付了求是学院资产的经济代价,被上诉人有权依法继受取得求是学院的资产。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接管求是学院,实质为履行收购的合意,是从实体上对双方某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定性。但就接管的来由而言,是因2006年6月求是学院发生学生集体上访事件,被上诉人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指令而接管求是学院的。接管工作均按照政府文件执行,求是××所称应当先评估,再支付转让价,最后再进行交接的程某,不符合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中合法、有序交接,妥善安置在校学生,确保平稳过渡,维护校园稳定的精神和要求,事实上也无法履行。此外,至本案一审时被上诉人已清偿了求是学院债务近1亿元,实体上已为取得求是学院资产支付了相应的经济代价。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向其支付资产对价即占有求是学院资产构成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求是××称求是学院具有净资产65700162.33元,完全与事实不符。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系求是学院为申报年检单方要求出具的意见,其依据的是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原始的会计凭证和资料,不具有证明力。该报告的基准日分别截止至2005年4月和2005年12月,与本案接管之日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浙万会专(2006)315号《专项审计报告》,反映了求是××对求是学院出资款的真实来源和构成,求是××没有分文投入;提交的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求是××无依据占用求是学院资产13738854.25元;提交的2007年8月27日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证明接管求是学院资产100588409.35元、负债137585744.16元,净负债36997334.81元,也确认了求是××应付求是学院共计13738854.25元的事实。虽然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浙万会专(2006)315号《专项审计报告》系刑事侦查中的鉴定意见,但该鉴定查证了相关原始凭证和书面文件,并且与高×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反映本案的客观真实情况,求是××不能提出相反证据,应当予以认定。而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是由求是学院法定代表人孙某某签署委托书,同意授权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清产核资工作组,委托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以后得出的结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对求是学院的货币资金、应收帐款、固定资产、存货等资产进行了核实,并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现场实物清点核对,履行了必要的验证程某。孙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申请注销求是学院时,也未提出异议,《专项审核报告》同样应当予以采信。四、通用××作为求是××的实际控制人,抽逃求是××的资金,应当对求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求是××对求是学院没有投入,还无理由转移、占用求是学院资金,构成对求是学院的不当得利之债,被上诉人承继求是学院债权债务,有权向上诉人追偿。根据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求是××应付求是学院13738854.25元。综上,请求驳回求是××的上诉,维持原判。
中××信托对于求是××的上诉,没有意见;但其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中××信托与通用××、高×之间关系不能视为代理关系,一审法院以代理关系进行认定,违反了民法通则、公某法、信托法之法律规定,属定性错误。上诉人与委托人签订的资金信托合同明某某定了对信托资金投资形成的股权的管理职责划分。上诉人仅能根据资金信托合同及其委托人的指令委派董事,行使股东权利,对委托人的指令上诉人仅对其形式合法性予以审核,并不参与具体的实际经营管理。无论是资金信托合同还是求是××章程及信托法之规定,均得不出求是××总经理具体的经营管理行为系信托事务的结论。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推荐高×为求是××总经理候选人,高×同时为通用××法定代表人就认定上诉人将股东权利义务转移给通用××,并进而推断认为上诉人与通用××因此形成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根据资金信托合同约定,上诉人仅是名义股东,并不参与求是××的实际经营管理,也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通用××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通用××的代理行为而判令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根据。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以所谓“合意”方某某受求是学院,显系错误。根据省教育厅《关于浙江科技学院求是应用技术学院终止办学有关事项的复函》意见,被上诉人须某行资产评估和支付对价义务后,才能接管求是学院,在被上诉人未履行上述义务前,被上诉人不享有求是学院的任何某某,被上诉人无诉权。(二)对抽逃注册资本的事实认定错误。所谓注册资本的抽逃,应是公某经营期间,因股东抽逃资金的行为,造成公某资本的实质性减少。本案中,缺乏抽逃注册资本1200万元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通用××在求是××成立的第二天转走了求是××所有的出资,这一时点来判定通用××在求是××中存在注册资本抽逃是错误的。三、本案证据认定上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据以认定的审计报告缺少审计报告应具备的透明、公某某定要求。其次,万某某计师事务所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其资产负债确认的原则存在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其主要项目的说明是建立在所谓清产核算小组的确认基础上,同样不具备客观、公正性。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外国语××答辩称:1、中××信托与通用××签订了资金信托合同,双方成立单一的资金信托合同关系,不能免除作为受托人根据信托法应该承担的法定义务。2、根据资金信托合同的规定,中××信托应该承担其对求是××的股东义务。3、中××信托应该按《公某法》的规定承担股东义务,如实出资保持公某资本金的稳定。4、中××信托将求是××的日常事务管理和控制权转移给通用××,构成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处理的情形。5、上诉人中××信托针对一审事实认定和证据的采信提出的上诉理由和事实相互违背,不能成立。一审认定通用××和中××信托之间成立代理关系,中××信托应该对通用××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信托的上诉,维持原判。
求是××、通用××针对中××信托的上诉均表示没有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某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某:教育学院于2010年7月27日更名为浙江××学院。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求是××是否存在没有合法根据而占用求是学院资产的行为。求是学院终止办学后,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因刑事案件侦查需要,在浙江省教育厅提供的求是学院的有关账簿、凭证等资料的情况下,委托浙江万某司法会计某某事务所、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有限公某对求是××对求是学院的出资情况、求是××注册资本情况、求是××经营的资金来源、使用情况及去向等事项进行了专项审计。根据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记载,求是学院和求是××之间资金流入、流出轧抵后,求是××应付求是学院人民币13738854.25元。并明确求是××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于2002年12月3日公某注册成立后次日即被转出。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亦记载,求是××对求是学院未实际出资。此外,时任求是学院法定代表人孙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省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组成清产核资工作组,该清产核资工作组委托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有限公某作了专项审核。审计机构在核实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凭证、帐册,并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现场实物清点后作出审核意见。孙某某作为求是学院的法定代表人在求是学院办理注销登记时,也未提出异议。该审计结论应予采信。而求是××一审提供的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无相关原始凭证印证,且报告的基准日分别为截止2005年4月和2005年12月,不足以反驳原教育学院一审提供的3份审计报告作出的审计结论。通用××法定代表人高×的笔录虽系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中制作,但其陈述能与审计报告查证意见相印证。综上,求是××转移、占有求是学院13738854.25元资金,无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求是××应将该款项返还求是学院的债权债务继受人教育学院,因教育学院已更名为外国语××,原教育学院在本案中的相关权利义务由外国语××继受。(二)中××信托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问题。中××信托依据其与通用××签订的资金信托合同,与通用××存在信托法律关系。按照资金信托合同约定,通用××将其所有的1200万元资金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中××信托用于求是××的股权投资。据此,作为信托受托人的中××信托,其义务在于接受委托人通用××提供的1200万元资金向目标公某出资,中××信托在受托人的管理权限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中××信托根据信托文件及求是××章程的规定,向求是××委派了高×作为公某的董事兼总经理。根据《公某法》规定,经理对公某董事会负责,其职责包括负责公某的经营管理工作等。一审法院认为中××信托将其对求是××的股东权利义务完全转移给通用××行使,缺乏证据支持。但中××信托以自己的名义担任股东,负有保证出资款真实且稳定的义务。相对于求是××及相关债权人而言,中××信托即是登记于公某登记机关的求是××的股东,尤其是从债权人的角度,更无从区分求是××注册资本被抽逃的行为是公某实际经营人的行为,还是登记股东的行为。高×系中××信托委派,其又是通用××的法定代表人,鉴于高×的双重身份,1200万元出资款在求是××成立后次日即被抽回到通用××,该抽逃出资的行为应认定为中××信托作为登记股东的行为。依照我国公某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公某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之规定,中××信托应在抽××内对求是××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信托以出资款来源于通用××,以其与通用××之间存在的内部关系对抗相关债权人,其主张不能成立。由于1200万元出资款在求是××成立后即被转回通用××帐户,故通用××应在1200万××内与中××信托共同对求是××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求是××的一审反诉诉讼请求能否成立。求是××一审反诉提出由被上诉人支付对价65700162.33元或返还相应财产的请求,其依据的是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根据前述理由,该审计报告不足以认定至2005年12月31日求是学院尚有净资产65700162.33元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原教育学院接管之日求是学院的资产状况。根据查某的事实,截止2006年8月31日,求是学院的净资产为负值,求是××要求外国语××支付对价或返还财产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正确。综上,该院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08)杭乙一初字第1740号民事判决第一、四、五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二、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08)杭乙一初字第174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中××责任公司、浙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1200万××内对浙江××实业有限公司所负的13738854.25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89384元,由浙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85151元,由中××责任公司负担104233元。
求是××不服终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本案系求是××与教育学院就求是学院接管事宜形成的整体收购关系,双方应就求是学院的整体资产状况,依法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鉴定、评估,原审法院仅依据教育学院单方提供的净资产审计报告和未经定案的刑事侦查程某中经公安机关委托作出的关于资金来源、使用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就作出判决,显然错误。截止2005年12月,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求是学院的净资产已达65700162.33元,教育学院提供的审计报告却显示截止2006年8月31日求是学院净资产为负值,其数据结果与实际情况及申请人一方提交的审计报告相差甚远。原审法院对求是××两次专门提交的另行评估、审计的书面申请均不予准许,不仅直接剥夺了求是××在程某上的诉讼权利,也使其实体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此外,原审法院割裂了教育学院主张的“不当得利”诉讼请求与求是××主张求是学院净资产对价的反诉请求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求是学院资产状况未经依法评估、确定的情况下,单独剥离部分债务,并作出返还不当得利款的判决,法律适用有误。综上,请求再审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外国语××(原教育学院)的诉讼请求,支持求是××的原审反诉请求。
被申请人教育学院答辩称: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经求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某的授权和确认,对求是学院的资产进行了逐一核实,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浙万会专(2006)315号《专项审计报告》与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虽系刑事侦查中的鉴定意见,但该鉴定意见查证了相关的原始凭证和书面文件,与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能相互印证,能够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求是××不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否定,该二份报告具有足够的证明效力。求是××提供的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系求是学院为申报年检单方要求出具的意见,不具有证明力,且该报告的基准日与本案确定的基准日不同,与被申请人接管求是学院时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关联性。此外,根据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求是××对求是学院不仅没有分文某某投入,反而任意转移、占用求是学院资金共计13738854.25元。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求是学院作为民办学校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求是××作为举办人并不能任意将学院财产占为己有。本案中,申请人占用求是学院资金没有合法根据,构成对求是学院的不当得利。作为求是学院的继受者,被申请人已经承担了求是学院对外负债1.3亿余元,其有权要求求是××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据此,请求驳回求是××的再审申请,维持原生效判决。
中××信托亦不服终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判认定求是××成立后其资金划转至通用××的行为为抽逃注册资本没有法律依据。无端扩大股东职责,要求股东为其提名出任被投资企业总经理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负责,这一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依据《公某法》的有关规定,经营层的行为后果由公某承担,公某股东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经营层行为如有不当,由经理个人对公某承担责任。混淆信托法层面的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也混淆委托人行为与受托人行为,原审判决结果错误地将委托人通用××的行为等同于受托人中××信托的行为,缺乏依据,也与信托法理及实践相违背。综上,中××信托不存在抽逃公某注册资本金的行为,请求再审法院撤销二审判决,改判中××信托无须为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申请人教育学院答辩称:中××信托投入求是××的资本金为1200万元,但在求是××验资完成的次日即被抽走,这一事实有打款的原始凭证为据并经司法鉴定机构审核确认,也与中××信托委派到求是××担任总经理一职同时也是通用××法定代表人高×的陈述相互印证。中××信托对浙万会专(2006)315号、浙万会审(2007)29号审计报告和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的异议缺乏相反证据,不能成立。中××信托作为求是××股东,依法应承担股东义务,如实出资并保持公某资本稳定。但事实上中××信托并未履行其作为股东的义务,而是将求是××日常管理和控制权转移给通用××,构成信托事务委托“他人”处理。根据《中华某某共和国信某某》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中××信托怠于履行受托人担任股东的义务,导致通用××将求是××资本金抽走,中××信托当然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综上,中××信托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中××信托的再审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
原审被告通用××对求是××和中××信托申请再审的意见表示认同,并提出外国语××收购的是求是学院而不是求是××,求是学院和求是××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即使求是××的股东存在抽逃资金行为,也与外国语××无关。外国语××要求求是××的股东承担法律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再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二审查某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某,二审判决后,中××信托已与外国语××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即外国语××同意中××信托向其支付执行款200万元后,不再追究其其他款项的强制执行义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浙万会专(2006)315号《专项审计报告》、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和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可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申请人求是××主张求是学院净资产65700162.33元的事实是否成立?三、中××信托应否在出资限额内对本案中抽逃注册资本金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经审理认为,求是学院为民办学校,主要依靠学院自身举债和国家投入办学。本案中原教育学院接管求是学院系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规定,与一般的资产收购行为在起因上和财产所有权归属上应有本质区别。2006年6月,求是学院因管理混乱引发学生大规模到省政府上访,求是学院向浙江省教育厅提出终止办学申请,后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和决定,教育学院才直接全面接管了求是学院。但鉴于求是××未配合教育学院进行资产清算和人、财、物的交接,省教育厅根据省政府文件要求,组织省财政厅、审计厅、教育学院等相关部门人员成立求是学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委托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对求是学院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专项审核,并作出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对此,时任求是××及求是学院法定代表人孙某某曾签署委托书,同意授权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清产核资工作组,委托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对求是学院资产进行专项审核。审计机构在核实相关原始凭证、账册并对固定资产进行了现场实物清点后作出的审核意见,已经征得了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孙某某的授权和确认。该专项审核报告证明求是学院资产100588409.35元,净负债36997334.81元,也确认了求是××应付求是学院13738854.25元的事实。孙某某在事后签署求是学院注销登记申请表时,对上述专项审核报告中的相关结论并无异议。由此,申请人求是××以其未参与求是学院资产的鉴定、评估程某否认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的效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清产核资工作小组组织委托财务清算的结果对求是学院具有约束力。至于浙万会专(2006)315号《专项审计报告》和浙万会审(2007)29号《专项审计报告》,虽系刑事侦查程某中形成的鉴定意见,但该鉴定查证了相关原始凭证和书面文件,与求是××经理高×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反映本案的客观真实情况,即求是××未对求是学院有实际出资。在申请人不能提出相反证据否定上述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原一、二审采纳该两份报告的证明效力,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申请人称求是学院具有净资产65700162.33元,其依据的是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2月24日出具的杭英审字(2006)第144号《审计报告》。但该《审计报告》中已明确表述,报告系求是学院为申报年检单位要求而出具,其依据的是求是学院提供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原始的会计凭证和资料,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力。并且该审计报告的基准日为2005年12月31日,也与本案中求是学院被接管之日的资产负债状况缺乏关联性。至于求是学院的全部资产,学院清产核资工作小组委托浙江万某某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浙万会专(2007)227号《专项审核报告》已经明确为净负债36997334.81元,在没有充足的、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申请人求是××关于求是学院净资产为65700162.33元的主张难以成立。此外,即使求是学院净资产为正值,根据《中华某某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求是学院作为民办学校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举办者在内都不能侵占学院的资产;同时《中华某某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二款明确,国家的资助、向学生收取的费用和民办学校的借款、接受的捐赠财产,不属于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出资。由此,求是××作为举办人对学院资产并不享有完整的财产权,其以杭甲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杭英审字(2006)第144号《审计报告》为据,要求原教育学院支付收购求是学院净资产对价65700162.33元或返还相关财产的主张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信托作为求是××的股东其应当按照公某法和公某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但本案中,中××信托除按委托人通用××的要求将1200万元资本金打入求是××及向公某委派董事、经理外,并没有实际履行任何管理、经营之责。根据本案查某的情况,求是××于2002年12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金为1500万元,其中中××信托认缴1200万元;但就在公某成立的次日,即2002年12月4日,中××信托委派的公某董事兼总经理同时也是通用××的法定代表人高×又将上述注册资本金全部抽逃转回通用××,其行为明显违反公某法和公某章程的有关规定。中××信托作为公某控股股东,本应依法维持公某资本金稳定,以确保债权人利益。但中××信托没有依法履行相应股东职责,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否则,委托人可能利用信托制度存在的不健全之处规避法律责任,造成权责失衡或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不良现象。事实上,根据中××信托和通用××双方自己签订的《资金信托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在浙江××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后,乙方(即中××信托)按照《中华某某共和国公某法》、公某的章程及甲方(即通用××)的义务行使股东权利和义务”,“如乙方认为甲方的意愿违反《中华某某共和国公某法》、浙江××实业有限公司的章程、或可能会损害乙方权益的,乙方有权拒绝实施,甲方不得有任何异议”--中××信托的股东责任也绝非提供一个资金往来账户,将信托资金打入公某账户这么简单,而是应该按照公某法、公某章程完整履行公某股东义务。本案中,无论中××信托派出的董事周某、姚兵,还是通用××法定代表人高×,均承认中××信托从未过问公某的资金调度,从未参加公某的董事会,履行董事职责。其放弃公某股东职责的行为对公某资本金在成立次日即被抽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据公某法股东须维持资本金稳定的规定,原审认定中××信托在其认缴注册资本金的范围内对通用××抽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况且,中××信托已就二审生效判决与外国语××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再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不符法律规定。
综上,申请再审人求是××、中××信托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某某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民终字第64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向阳
审 判 员
王红根
代理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妍
吴晓颖与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等追索代付款纠纷上诉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9)浙商终字第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晓颖。
委托代理人:孙进桥。
委托代理人:应美群,永康市经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正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傅晓云,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勇,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康市良宝动力工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福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福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颖果。
委托代理人:胡新洪,浙江五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晓颖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歌化学公司)、永康市良宝动力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宝工具公司)、吴福舫、吴颖果追索代付款纠纷一案,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金中民二初字第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吴晓颖的委托代理人孙进桥、应美群,兰歌化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勇、傅晓云,良宝工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福舫,吴福舫、吴颖果及其委托代理人胡新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兰歌化学公司为良宝工具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因良宝工具公司到期未履行还款义务,兰歌化学公司分别被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金中民二初字第15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应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在借款本金500万元、利息7204.61元及逾期利息和律师代理费4684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此兰歌化学公司为良宝工具公司向该行偿还了人民币6330517.92元;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金中民二初字第160号民事判决判应令向中国工商银行永康市支行在借款本金5985100元、利息及律师代理费52750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金中民二初字第199号民事判决判令向中国工商银行永康市支行在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3058471.21元、罚息、复利及律师代理费34840元范围内的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因上述两判决,兰歌化学公司为良宝工具公司向该行偿还了人民币共计5668643.32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杭民二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判令应向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在借款本金495万元、利息、逾期利息及律师代理费用25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此兰歌化学公司为良宝工具公司向该行偿还了人民币20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人民币13999161.24元,良宝工具公司均未向兰歌化学公司偿还。良宝工具公司因未能参加工商年检被永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6年11月吊销营业执照。另查明,吴福舫、吴晓颖、吴颖果系良宝工具公司的股东,2004年2月该公司进行增资,吴福舫的出资从560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吴晓颖的出资从246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在增资过程中吴福舫、吴晓颖抽逃了其所增的出资。
原审法院认为,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兰歌化学公司依据人民法院的判决、调解向良宝工具公司的债权人共计偿还人民币13999161.24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良宝工具公司应依法向该公司归还上述款项。兰歌化学公司要求良宝工具公司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其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保持不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股东不得抽逃其出资。2004年2月在良宝工具公司增资过程中,该公司股东吴福舫、吴晓颖抽逃了其所增加的出资,其行为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对公司债务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兰歌化学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吴颖果有抽逃注册资本的事实,故兰歌化学公司要求其对良宝工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对兰歌化学公司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良宝工具公司、吴福舫、吴晓颖经原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系其对法律的不尊重及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作出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之规定,2008年10月18日判决如下:一、良宝工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兰歌化学公司担保代偿款人民币13999161.24元;二、良宝工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兰歌化学公司利息损失(算至2007年10月30日止为779566.02元,以后的利息损失按本金13999161.24元,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付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吴福舫在人民币640万元的范围内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吴晓颖在人民币1354万元的范围内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兰歌化学公司要求吴颖果对被告良宝工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0472元,由良宝工具公司、吴福舫、吴晓颖共同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吴晓颖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只向吴晓颖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其他法律文书如开庭传票、吴颖果答辩后有关证据及判决书等文书公告送达。且未将公告送达到吴晓颖家庭住址所在地法院、街道、村委会或居委会等。由于一审法院在送达程序上违法,使吴晓颖失去了一审诉讼权利。增加了吴晓颖的诉讼费用及浪费了诉讼资源,应依法发回重审。二、认定证据错误,事实不清,导致本案错判。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六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吴晓颖与被上诉人良宝工具公司、吴福舫、吴颖果共同策划增资。实际上增资全过程都是兰歌化学公司的程外明一人操作的。吕盛荫作为良宝工具公司的职工跟着协助处理。上诉人吴晓颖在企业增资过程中确实在新加坡留学,所以2004年2月该公司增资吴晓颖是不知道的,也没有人同上诉人讲过。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2月1日公司增资申请、2月1日股东会决定、2月12日出资声明书、2月12日发起人股东名单、2月12日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等六种文书上签名均不是吴晓颖所书,也不是吴晓颖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吴晓颖作为吕盛荫妻子,应认定吴晓颖具有抽逃资金的事实”的推理是错误的,所作出判决是错误的。其上诉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
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原审法院送达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多方了解吴晓颖的下落未果,原审法院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符合民诉法的规定,且在公告栏中张贴的方式并无不当。吴晓颖和吴颖果是兄妹关系,吴颖果已委托律师出庭,从常理上看也未妨碍吴颖果的诉讼权利。应认定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是主动放弃诉讼权利。二、吴晓颖作为良宝公司的股东,应该知道增资及抽逃出资的事实,有其父母的证明,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原审法院认定吴晓颖抽逃出资的事实正确。三、原审法院认定吴颖果未抽逃出资,并据此驳回诉请,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保留申诉的权利。其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良宝工具公司、吴福舫答辩称:公司已破产,资产已被拍卖。子女根本没有钱拿出来出资。公司其实都是我和老婆一起作主的,写自己子女的名字,是防止以后减少矛盾。增资是因为公司要为兰歌公司作担保人,增资本身是虚假的。
被上诉人吴颖果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吴颖果本人有关起诉状、证据材料本身的送达是合法的,判决书中驳回兰歌公司要求吴颖果对良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
二审中,上诉人吴晓颖提出《申请笔迹鉴定报告》,要求对良宝工具公司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2月1日公司增资申请、2月1日股东会决定、2月12日出资声明书、2月12日发起人股东名单、2月12日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上述六份文书上的吴晓颖签名的真实性予以鉴定。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提出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本院调取:吴晓颖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的出入境记录。
上诉人吴晓颖在二审中提供四份证据,即:证据1,李春菊的询问笔录。拟证明2004年公司增资时吴晓颖未参与商量。证据2,亚太商学院公证书。拟证明吴晓颖在2003年10月27日至2004年12月在新保波亚太学院留学。良宝工具公司的增资、抽逃资金等整个过程,吴晓颖均未参与商量过。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2月1日公司增资申请、2月1日股东会决定、2月12日出资声明书、2月12日发起人股东名单、2月12日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上签名均不是吴晓颖所书的事实。证据3,永康市东城街道许马头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和证据4,吴晓颖、吕德胜居民户口簿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吴晓颖与公公吕德胜、婆婆李梅珍同住九铃东路3233弄1幢的事实。
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提供二份证据,证据1,共同承担债务协议一份及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两份。拟证明:(1)共同承担债务协议及吴晓颖、吴颖果印章的真实性业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2)吴晓颖在2004年11月3日即良宝工具公司增资后以股东身份履行义务。吴晓颖、吴颖果知道增资及抽逃出资的事实。证据2,股东会决议、申请变更报告、永康市良宝动力工具有限公司章程。拟证明吴晓颖一直以来使用的私章与增资时所盖的私章系同一枚。
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质证认为:对李春菊的询问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三个股东都是一家人,因此不能证明吴晓颖未参与商量。且这份证据上的“吴晓颖”签名是由吕盛萌代签的。证据2,亚太商学院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吴晓颖本人在国外,也不能证明吴晓颖不知道。证据3、4,永康市东城街道许马头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该单位作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采信。至于吴晓颖与公公、婆婆一起居住的事实,是否真实我司有异议。且户籍并不能证明吴晓颖一直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上诉人吴晓颖对被上诉人兰歌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证据1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对共同承担债务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只有法人代表的吴福舫的签字,吴晓颖、吴颖果都没有签字,只有盖章,公章是公司保管并被加盖,吴晓颖本人并不知道。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
被上诉人良宝工具公司、吴福舫对上诉人吴晓颖提供的证据和兰歌公司提供证据的待证事实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吴颖果对上诉人吴晓颖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对兰歌公司提供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吴颖果的签字,吴颖果对该协议的达成是未知的。兰歌公司提供的二份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的。
本院认定:上诉人吴晓颖在二审中提供四份证据和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提供二份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不持异议的予以认定,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二审查明: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上加盖的吴晓颖私章系其留在公司财务保管的章。据吴晓颖二审提供的证据李春菊(系吴晓颖母亲)在永康市公安局2005年5月31日14时30分讯问笔录,虽其拟证明2004年公司增资时吴晓颖未参与商量。但是,其母亲李春菊在笔录中也陈述公司增资具体都是吕盛荫负责办的。结合已生效的永康市人民法院(2005)永刑初字第7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认定吴晓颖名下的增资及抽逃出资系吕盛荫在具体办理。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追偿的欠款数额均无异议,兰歌公司对吴颖果免责也未提出上诉,上述问题均不作二审审查范围。本案争议焦点: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吴晓颖对抽逃出资是否承担责任。(一)经查:原审法院于2007年11月7日以特快转递分别向吴晓颖、吴颖果户籍上载明的住址、良宝工具公司营业执照上记载的地址邮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资料,向良宝工具公司邮寄的信件因无法送达被邮局退回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07年11月22日公告向吴晓颖、吴颖果、良宝工具公司送达上述诉讼资料及2008年2月27日开庭。又于2008年2月27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吴晓颖等2008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原审法院在未收到吴晓颖退回的送达回证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开庭通知,程序上是合法的。公告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通知到当事人。况且,吴颖果已准时到庭,参加了一审庭审。吴晓颖和吴颖果系姐弟关系,通常情况下,吴颖果没有理由向吴晓颖隐瞒法院公告通知开庭。吴晓颖以此提出一审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本案吴晓颖名下的出资从246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此后又抽逃了所增出资,对此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据吴晓颖二审提供的证据李春菊(系吴晓颖母亲)在永康市公安局讯问笔录,其母亲李春菊在笔录中也陈述公司增资具体都是吕盛荫负责办的。结合已生效的永康市人民法院(2005)永刑初字第7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其在上诉状这也自认吕盛荫参与办理,可以认定吴晓颖名下的增资及抽逃出资系吕盛荫在具体办理。吴晓颖对丈夫吕盛荫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1)永康市良宝动力工具有限公司被增资后提高了公司向银行贷款额度,表面上是公司受益,实质上是股东受益,吴晓颖作为股东也不列外。此外,吕盛荫增资后又抽逃出资是为公司所为,并非用于个人事务。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上加盖的吴晓颖私章系其留在公司财务保管的章。吴晓颖称此期间其在国外读书,但并非属下落不明,况且吴晓颖和吕盛荫也非夫妻关系不好,吴晓颖和父母之间也不存在关系不好,故在现代通信发达的时代,他人有理由相信吕盛荫的所为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2)吴晓颖未举证在2000年8月(即其与丈夫吕盛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良宝工具公司变更成立时,吴晓颖名下的股份系其个人婚前财产。2004年,吕盛荫作为丈夫对吴晓颖名下的股份进行增资及抽逃出资等,系属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共同共有财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夫妻双方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3)本案兰歌公司追偿的系其已为良宝工具公司清偿的债务,作为良宝工具公司的股东本身就应对公司负责。据上,吴晓颖和丈夫两人对抽逃出资部分应承担连带责任。现被上诉人兰歌化学公司选择夫妻一方吴晓颖对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判令吴晓颖在抽逃出资部分范围内承担责任正确。吴晓颖上诉称对增资和抽逃出资不知情,也非其所为,故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吴晓颖和兰歌化学公司分别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和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本院认为,吴晓颖在良宝工具公司2004年2月2日的公司章程、2月1日公司增资申请、2月1日股东会决定、2月12日出资声明书、2月12日发起人股东名单、2月12日企业申请登记委托书上述六份文书上的吴晓颖签名即使不是其本人亲笔所签,也不影响其责任的承担,故已无鉴定必要。至于兰歌化学公司提出调取吴晓颖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的出入境记录,也无实际意义。对上述两方当事人的申请均不予准许。
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上诉人吴晓颖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72元,由上诉人吴晓颖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梅
审 判 员 杜 正 民
代理审判员 王 丽
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吕 俊
吴艳艳等诉永嘉艳阳纸箱有限公司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浙03民终60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艳艳。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宇辉,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婷,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永嘉艳阳纸箱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马文兵,该公司管理人的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晓哲,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艳艳与被上诉人永嘉艳阳纸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阳公司)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4民初4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艳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艳阳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吴艳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名义股东,未实际出资或参与经营管理,且涉案银行卡实际由他人使用,系事实认定错误。吴艳艳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银行卡为公司使用,相应的款项也没有用于吴艳艳个人。(1)吴艳艳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反映了艳阳公司与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布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吴陈雷,其实际控股分别达80%、98%,公司的经营运作均在吴陈雷的控制下,吴艳艳提供的《电子银行交易回单》证明两家公司之间存在交易,出庭作证的证人亦证明艳阳公司系阿布啦公司的材料供应商,两公司之间交易往来频繁,该些情况足以证明两家公司为关联企业。(2)吴艳艳在一审中提供的《香港阿布啦食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阿布啦公司)对账单》证明涉案的农业银行卡为阿布啦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香港阿布啦公司经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查询并不存在,香港阿布啦公司实际上就是阿布啦公司,而且该对账单上盖有阿布啦公司的公章,公司公章作为公司处理内外部事务的印鉴,盖了公章的文件即具有法律效力,代表公司的行为并承担一定的责任。如香港阿布啦公司与阿布啦公司实际上不是同一家公司,则阿布啦公司必然不会将自己公司的印章随意提供给别的公司使用,因此,对该份《对账单》的真实性是可以确认的,同时亦证明了涉案的农业银行卡为阿布啦公司的指定收款账户,不作为吴艳艳个人银行卡使用。(3)庭审中,证人高某、吴某1、尤某、吴某2、周某均述称知晓吴艳艳的农行卡是供吴艳艳使用的,该卡亦一直存放在阿布啦公司出纳处,吴艳艳仅在开卡时以及开卡后应公司要求到银行打印对账单时才有接触,进一步证明该卡非吴艳艳个人使用。(4)从吴艳艳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看,涉案的所有款项均转入了案外人何圣华的招商银行账户内,证人尤某、吴某1、周某均证实,何圣华的招商银行卡亦是作为阿布啦公司的卡在使用。再结合吴艳艳提供的《汇款凭证》等材料可以看出,何圣华招商银行卡内的资金既有被用于阿布啦公司的货款汇给材料供应商,亦有作为艳阳公司的货款支付给材料供应商,或者用于公司其它往来款项。因此,艳阳公司所诉称的三笔款项并没有为吴艳艳个人使用,而是最终通过各种途径用于吴陈雷控制的两家关联企业。二、一审法院认为“吴艳艳有无将涉案个人银行卡交他人使用,均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是错误的,对吴艳艳也是不公平的。吴艳艳没有将涉案的银行卡交由其他任何个人或者本人使用,而是自开卡后一直由阿布啦公司使用,所有的款项往来吴艳艳均不知情。涉案款项经查证后,均用于艳阳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其后果应由使用该款项的公司承担。另,吴艳艳认为,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必须是股东侵占了被投资企业的财产,本案涉案的款项转到吴艳艳名下的农业银行卡后根本不在吴艳艳的控制之下,更谈不上将款项占为己有。同时,如果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则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必然会造成影响,并严重损害公司的权益。本案涉案的款项被用于支付艳阳公司的货款等用途,对艳阳公司及阿布啦公司来说,为日常的经营所需及惯用的对外支付方式,对公司本身没有造成损害。
艳阳公司辩称:一、吴艳艳系艳阳公司股东的事实是清楚的,应依法承担股东责任。本案中艳阳公司的基本户发生过三笔交易,从公司拿走共计702710元。公司财务吴某1表示对该三笔交易并不知情,也没有入公司账目。至于转账后吴艳艳如何使用该款项与公司不具有关联性。二、吴艳艳将艳阳公司基本户的资金转入个人账户并不归还的行为减弱了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另外吴艳艳作为公司股东,若明知存在明知抽逃出资仍予以配合的话应承担连带责任。三、吴艳艳与案外人的经济纠纷不影响本案艳阳公司对吴艳艳抽逃出资的追收。艳阳公司与阿布啦公司在工商登记中都是互为独立的法人,两家企业均已进入破产程序,阿布啦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破产终结,两家公司均未提供账册给破产管理人,故无法通过财务数据看出两企业是否存在混同的情况。破产程序是不可逆的,如吴艳艳权利受损,应另行救济。吴艳艳的侵权行为事实清楚,吴艳艳未能说明该三笔款项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未将款项偿还艳阳公司,侵犯了艳阳公司的偿还能力,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艳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艳艳立即归还艳阳公司其抽逃的出资款70271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实际抽逃出资之日起按年利率5.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吴艳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艳阳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注册成立,系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50万元,吴艳艳任法定代表人。2013年9月12日艳阳公司章程第六条约定:公司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为:吴艳艳出资为人民币90元,占注册资本的60%;其中以货币方式出资90万元;于2013年9月23日前缴足……吴艳艳在章程全体股东签名处签字。2013年9月23日温州中易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当日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各股东以货币出资。2013年11月22日、12月2日,艳阳公司从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12×××27)以借款名义分别转账10万元、28万元至吴艳艳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14);2014年1月2日又以往来款名义转账322410元至吴艳艳账户。2015年10月30日,吴艳艳与吴陈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在艳阳公司拥有的90万元股权转让给后者,并于同日办理投资人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此后由吴陈雷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以(2016)浙0324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东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艳阳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艳阳公司管理人。管理人经调查发现,吴艳艳未与艳阳公司发生货款或交易往来的情况下,总计702710元先后以借款、往来款名义从艳阳公司账户转账至吴艳艳个人账户且至今未归还。艳阳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等方式抽逃出资。吴艳艳作为艳阳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缴纳出资90万元到位后,总计702710元以借款、往来款名义从艳阳公司账户转入其个人账户,而吴艳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公司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上述款项至今未返还公司,客观上构成了抽资的后果,吴艳艳应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吴艳艳辩称系艳阳公司名义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或参与经营管理,且涉案银行卡实际由他人使用。首先,对于上述抗辩,吴艳艳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吴艳艳在艳阳公司章程签字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表明其具有被登记为艳阳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并已完成出资,相应信息均已在公司登记机关完成登记,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对外公示性;吴艳艳有无将涉案个人银行卡交他人使用,均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故吴艳艳的上述抗辩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艳阳公司要求吴艳艳返还出资款70271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吴艳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艳阳公司返还出资款70271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5.6%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其中100000元的利息自2013年11月22日起算,280000元的利息自2013年12月2日起算,322410元的利息自2014年1月2日起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27元,减半收取5413.5元,由吴艳艳负担。
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吴艳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户籍证明一份,拟证明吴陈雷与吴陈云系同一人,相关合同上签署的“吴陈云”为阿布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陈雷。2.《房屋租赁合同》一份,3.证明一份,4.领款凭证、转账凭证各三份,证据2-4拟证明由阿布啦公司租赁永嘉县瓯北镇三桥工业区厂房作为艳阳公司的办公场所,并支付租金,两公司为关联企业。5.《瓦楞纸板销售合同》一份,拟证明永嘉艳阳纸箱负责人为吴陈雷,对外签订合同经吴陈雷签字同意。6.证明一份,7.关于做好公司车间管理工作的通知一份,证据6-7拟证明阿布啦公司与香港阿布啦公司系同一家公司,与艳阳公司为关联企业,实际控制人均为吴陈雷。8.1月份食堂结算清单汇总一份,9.阿布啦通字【2014】18号文件一份,证据8-9拟证明阿布啦公司的管理人员同时负责艳阳公司日常管理经营,两者为关联企业。10.债权汇总表一份,11.企业信用公示信息一份,12.领款凭证五份,第10-12项证据拟证明阿布啦公司曾向艳阳公司的债权人支付艳阳公司欠付的货款,两者为关联企业。13.证明书一份,14.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一份,15.阿布啦公司指定打款账号说明一份,16.谈话笔录一份,证据13-16拟证明吴艳艳卡号为62×××14的农业银行卡为公司使用,非个人使用。17.香港阿布啦公司北区副总岗位职责证明一份,拟证明该文件所盖的公章为阿布啦公司公章,两公司实为同一家企业。18.证人王某的证言,拟证明阿布啦公司跟香港阿布啦公司是兄弟企业,阿布啦公司和艳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都是在吴陈雷。
艳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民事裁定书二份,拟证明案外人阿布啦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从程序上说两家企业已经分别破产并且阿布啦公司破产已经终结,浙江天成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已经申报了两笔债务。
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艳阳公司对吴艳艳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7、8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4、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5、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证据6的合法性没异议,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2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均是证明阿布啦公司和艳阳公司之间系关联企业,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首先两家企业在工商登记上是互为独立的个体,吴艳艳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为阿布啦公司,根据阿布啦公司的注册信息,其注册地营业地址是永嘉县,恰恰证明阿布啦公司曾租赁厂房供其使用,且领款凭证上没有记载具体信息。如果存在代付租金的情况,那么应当在破产时作为债权申报。浙江天成医药公司已经向永嘉阿布啦食品有限公司申报该笔租金961436.47元,这跟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证明是相冲突和矛盾的。若其认为租金实际是由艳阳公司产生的,应向艳阳公司申报该笔债权。因证人证言出具的时间都是近期产生的,可能受到他人影响,其证明力较弱。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14-17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3-16证明吴艳艳的银行卡是他人使用的,艳阳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3年9月23日,之前的证据是无法证明艳阳公司成立后产生的事实,吴艳艳是吴陈雷的外甥女,家族经营模式也是温州常见的,故其银行卡是否有借给他人使用是其的权利处分,因此产生的后果应由其自身承担。第17项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明的是案外人的经营管理。证据18,证人所说艳阳公司与阿布啦公司的房东不同,与艳阳公司的证据相矛盾;艳阳公司与阿布啦公司应当存在一定的经济往来,吴艳艳也是明知艳阳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流向的。吴艳艳对艳阳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异议,对浙江天成医药包装有限公司的90多万元的金额真实性没异议,但不能证明这90多万元就是租金,不能证明艳阳公司的待证事实。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吴艳艳提交的证据1-12、17、18证明的艳阳公司与阿布啦公司财产混同事实与本案争议的吴艳艳应否承担出资责任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该些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吴艳艳提交的证据13,只能证明本案诉争收取一笔2520元款项的事实;吴艳艳提交的证据14,存在消费、归集等项目,归集一般系归集本人或他人在本行或他行账户的资金,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明细流水非为吴艳艳使用;吴艳艳提交的证据15,该证据出具日期为2015年10月22日,迟于吴艳艳出资转出其账户的日期近两年,该证明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吴艳艳提交的证据16,系吴艳艳所作的陈述,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在无其他证据印证下,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综上,本院对吴艳艳提交的证据13-16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艳阳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阿布啦公司欠债2138795.62元而被债权人申请破产,后因阿布啦公司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而被永嘉县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查,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7年7月28日,永嘉县人民法院根据案外人李胜微的申请,受理阿布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申报确认,阿布啦公司共欠2138795.62元。2017年9月21日,永嘉县人民法院以阿布啦公司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为由,裁定宣告阿布啦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股东必须依法履行出资义务,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在公司成立之后,则同时构成公司法上的违法行为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有权向其追究责任。吴艳艳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明白在章程和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的法律后果。其在签名成为艳阳公司的股东后,不得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或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吴艳艳在缴纳出资90万元后,将总计702710元以借款、往来款名义从艳阳公司账户转入其个人账户。虽吴艳艳抗辩该个人账户非为其掌控,款项也非为其收取,但吴艳艳对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该账户由吴艳艳开设,除被盗用等非为吴艳艳行为造成的情况外,吴艳艳应承担该账户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即使吴艳艳存在出借个人账户的情况,亦不能免除吴艳艳归还702710元出资的义务。此外,吴艳艳作为工商登记持有艳阳公司60%股份的股东,在艳阳公司未能偿还债权人欠款经破产程序后由艳阳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吴艳艳追收抽逃出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不管其在本案中是名义股东还是实际股东均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吴艳艳抗辩其为名义股东无需承担责任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艳阳公司与阿布啦公司财产是否混同并不免除两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此属于艳阳公司与阿布啦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在阿布啦公司破产程序中,无人向管理人提供该公司的财产及会计资料,艳阳公司也未申报任何债权,无法查明本案诉争的702710元已经用于艳阳公司或归还艳阳公司。
综上所述,吴艳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为10827元,由上诉人吴艳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斌
审 判 员 周林环
审 判 员 黄丽君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日
代书记员 周瀚阳
桐乡市崇福宏王达裘皮制品厂等与嘉善诚洲企业登记代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侵害债权纠纷上诉案
桐乡市崇福宏王达裘皮制品厂等与嘉善诚洲企业登记代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侵害债权纠纷上诉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浙商终字第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桐乡市崇福宏王达裘皮制品厂。
负责人:王文康,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孙锡泉。
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增荣。
委托代理人:沈思敬,浙江天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善诚洲企业登记代理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敏文,
委托代理人:黄玉弟,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美勤。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忠华。
上诉人桐乡市崇福宏王达裘皮制品厂(以下简称宏王达厂)、顾增荣为与被上诉人嘉善诚洲企业登记代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洲公司)、杨美勤、顾忠华侵害债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嘉商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裕灿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徐向红、代理审判员孙光洁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1年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王达厂的负责人王文康及其委托代理人孙锡泉,上诉人顾增荣的委托代理人沈思敬,被上诉人诚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玉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美勤、顾忠华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2月,顾忠华、顾伟华欲成立嘉善金巴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巴蕾公司),商量由顾伟华和其女朋友杨美勤作为股东,找到杨美勤后,杨美勤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根据金巴蕾公司章程记载,顾伟华认缴出资40万元,杨美勤认缴出资10万元。诚洲公司代为办理金巴蕾公司注册登记手续,接受委托后指派史婷婷具体经办工商登记事宜。由于没有资金,顾忠华与史婷婷商量先让诚洲公司垫资5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顾忠华支付垫资款利息,在公司成立后即归还垫资。诚洲公司答应顾忠华的要求并提供50万元资金予以验资。2006年3月2日金巴蕾公司登记成立,之后诚洲公司经办人史婷婷随即将50万元从验资帐户转到金巴蕾公司的基本帐户,再以开支票的形式抽走注册资金50万元用于归还垫资。50万元注册资金抽走后,金巴蕾公司的股东顾伟华和杨美勤至今未补足各自的出资。2006年8月至11月,宏王达厂和金巴蕾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双方因货款未支付成讼,金巴蕾公司对欠宏王达厂货款1623566元没有异议,根据(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金巴蕾公司应支付宏王达厂货款162356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金巴蕾公司股东顾伟华因提供保证担保,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终审判决维持。在(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依法查封金巴蕾公司位于嘉善商城北五街8-10号仓库内的各式毛条26600条(按21.50元/条计算价值571900元)、各式羽绒服3580件(按96元/件计算价值343680元)、鸭绒约3吨(按3吨即3000公斤、170元/公斤计算价值51万元),合计价值1425580元。2007年9月,顾忠华擅自将查封的500件羽绒服作为抵债物品抵给上海琦慧德工贸有限公司。随后,顾忠华为筹集资金,伙同顾增荣将查封的2100件羽绒服及42包鸭绒作为抵押物向他人借款10万元。后顾忠华和顾增荣又将剩余的被查封物品转移至其他仓库。(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判决生效后,宏王达厂申请执行,2008年6月27日原审法院作出(2007)嘉中法执字第149号民事裁定,将追回的金巴蕾公司查封财产即1323.8公斤鸭绒、23600条小毛条、2040件男女各式羽绒服作价172000元抵偿给宏王达厂,顾伟华未履行给付义务。现尚有价值合计497294元查封财产未追回,具体为,羽绒服3580件-2040件=1540件,计款1540件×96元/件=147840元,各式毛条26600条-23600条=3000条,计款3000条×21.50元/条=64500元,鸭绒3000公斤-1323.8公斤=1676.2公斤,计款1676.2公斤×170元/公斤=284954元。2009年9月2日经终审裁定,顾忠华因犯虚报注册资本、合同诈骗、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等罪被判刑,顾增荣因犯虚报注册资本、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被判刑,(2009)浙嘉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中判定“未追回的被害人被骗财物损失,责令相关被告人退赔”。
2010年2月25日,宏王达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否认金巴蕾公司法人人格;2.诚洲公司承担50万元的赔偿责任;3.杨美勤、顾忠华对金巴蕾公司所欠宏王达厂货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顾忠华和顾增荣赔偿宏王达厂1208000元。诚洲公司答辩称:宏王达厂在(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案件中曾经以金巴蕾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人格为由,要求追加两股东为被告未获准许,宏王达厂仍以同一理由起诉金巴蕾公司股东,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应予驳回。诚洲公司并没有与顾忠华、顾伟华共同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犯罪行为,也没有串通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民事行为。诚洲公司为金巴蕾公司成立垫资50万元,属于一般民间借贷关系,宏王达厂要求诚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宏王达厂对诚洲公司的诉讼请求。杨美勤答辩称:(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已认定金巴蕾公司系独立法人,不予准许宏王达厂追加杨美勤为共同被告的要求,宏王达厂现起诉杨美勤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裁定驳回起诉。以股东虚假出资否认公司法人人格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股东出资不实,债权人只能要求股东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如果虚假出资,则股东负有补足出资的义务,债权人根据代位权理论也可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但责任范围以虚假出资额而非债权额为限。杨美勤只是金巴蕾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顾忠华,杨美勤不清楚金巴蕾公司和宏王达厂之间的业务,也没有以金巴蕾公司名义谋利,不应承担虚假出资的责任。宏王达厂因其经济损失追究了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其货款损失系犯罪行为所致,杨美勤不但没有参与犯罪,而且本身也是受害者。请求驳回宏王达厂对杨美勤的诉讼请求。顾忠华答辩称:由于金巴蕾公司当时有800多万元应收款未收回,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所以金巴蕾公司并非存心拖欠宏王达厂款项。顾忠华抵给金巴蕾公司债权人的查封财产只有500件羽绒服,按成本价每件100元计算只有5万元,其余查封的财产追回后已执行给了宏王达厂。顾忠华没有与宏王达厂发生业务,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顾增荣答辩称:宏王达厂与金巴蕾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已经法院判决并且执行,宏王达厂因执行不到就起诉他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顾增荣只是抵押和移动被查封的财产,并未处置查封财产,财产本身不会减少。执行时的财产估价低于查封金额,系由市场行情、长期查封等原因所造成,如查封财产时就以货抵款就不会有损失,因此金巴蕾公司财产贬值的损失应由宏王达厂赔偿。况且查封的财产属于金巴蕾公司所有,即便查封的财产减少,宏王达厂也无权主张。因此,顾增荣与宏王达厂既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损害赔偿关系,请求驳回起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宏王达厂在与金巴蕾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后,因金巴蕾公司拖欠宏王达厂货款未付,宏王达厂提起诉讼,金巴蕾公司对欠宏王达厂货款1623566元没有异议,该欠款虽经判决和强制执行,宏王达厂尚有货款145156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未获清偿,金巴蕾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金巴蕾公司现基本丧失清偿宏王达厂债务的能力,宏王达厂货款损失客观存在。货款从性质上说属于债权,债权既是一种重要的民事权益,也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重要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宏王达厂以其对金巴蕾公司享有的债权受到损害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诚洲公司、杨美勤、顾忠华和顾增荣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案件受理条件。案件争议的焦点是诚洲公司、杨美勤、顾忠华和顾增荣对宏王达厂的债权损失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
一、关于诚洲公司的责任问题。顾忠华、顾伟华欲成立金巴蕾公司,委托诚洲公司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诚洲公司为此指派史婷婷具体经手,因此,史婷婷办理金巴蕾公司工商登记的行为系代表诚洲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史婷婷职务行为的后果应由诚洲公司承担。由于没有资金,顾忠华通过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让诚洲公司垫资5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在金巴蕾公司成立后,诚洲公司根据事前与顾忠华协商好的意见,以支票形式从金巴蕾公司的基本帐户上抽逃注册资本50万元,以归还金巴蕾公司注册时诚洲公司帮助投入供验资用的借款。诚洲公司作为一个从事代理企业登记的单位,应明知注册资本的性质和用途,在股东没有投入的情况下提供资金成立金巴蕾公司,则该投入的资金即属于金巴蕾公司的财产。但是,诚洲公司却在金巴蕾公司成立后即与顾忠华等人一起抽逃已经属于金巴蕾公司法人财产的出资,用以偿还成立金巴蕾公司时用以出资的借款,使金巴蕾公司从成立一开始就因股东出资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责任财产,让金巴蕾公司股东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却披上“合法出资的外衣”,致与金巴蕾公司进行交易的主体处于危险境地。诚洲公司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包括宏王达厂在内的金巴蕾公司债权人的财产权益,诚洲公司在整个过程中行为主动,态度积极,诚洲公司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且诚洲公司的侵权行为与宏王达厂所受债权损失有因果关系。诚洲公司的行为等同于甚至严重于给金巴蕾公司出具虚假的验资证明,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验资机构出具不实或虚假验资报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和通知,诚洲公司应当在金巴蕾公司股东无法补足出资的金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作为金巴蕾公司两股东之一的顾伟华因提供保证担保,需对金巴蕾公司欠宏王达厂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范围大于顾伟华作为股东出资不到位的责任,对于宏王达厂的债权损失而言,单独认定顾伟华的股东出资责任已无必要。由于生效判决经强制执行后,顾伟华没有清偿过金巴蕾公司对宏王达厂所负的债务,顾伟华无法补足出资的事实成立,故诚洲公司对于股东顾伟华无法补足的出资金额40万元应当向宏王达厂承担赔偿责任。金巴蕾公司另一股东杨美勤责任及因此对诚洲公司承担赔偿金额确定的问题,随后阐述。
二、关于杨美勤的责任问题。在顾忠华和顾伟华设立金巴蕾公司时,杨美勤虽没有主动参与,但杨美勤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明用于工商登记,且在其后的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对于成为金巴蕾公司的股东,杨美勤并未表示出异议,杨美勤关于其完全属于错误股东的说法不能成立,因此可以认定杨美勤系金巴蕾公司的股东。但是,现既没有证据证明杨美勤参加了金巴蕾公司的筹建设立,也没有证据证明杨美勤参与了抽逃出资,更没有证据证明杨美勤以金巴蕾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杨美勤虽然是金巴蕾公司的股东,但杨美勤没有以金巴蕾公司为合法外衣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对事实上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征的法人状态的揭示来凸现隐藏于公司背后的人格滥用者,即股东无限责任对有限责任修正的效力仅仅及于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股东个人,而不及于公司其他未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法人人格否认是在特定情况下,在“由公司形式所树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钻一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也就是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通过刺穿法人面纱,或揭开法人面纱的一角,仅将个别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股东凸现出来,使其不再受法人独立人格这一面纱的遮挡和享受股东有限责任的庇护,从而将该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直接要求该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而对于其他未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法人这一面纱仍然存在着,并以法人的独立人格为屏障仍然以其对公司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宏王达厂于本案中诉请否认金巴蕾公司法人人格,实际以否认金巴蕾公司的法人人格为由要求杨美勤对金巴蕾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很显然,宏王达厂关于杨美勤需对金巴蕾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和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从金巴蕾公司的设立过程看,金巴蕾公司的注册资金系由诚洲公司垫付而来,杨美勤没有直接在金巴蕾公司成立时即缴清公司章程中其所认缴的出资金额;金巴蕾公司设立以后,杨美勤没有向诚洲公司偿还垫付的出资,在诚洲公司从金巴蕾公司抽回垫付的注册资金的情况下,杨美勤也没有补足其所认缴的出资金额。杨美勤作为金巴蕾公司的股东,出资不到位的行为使金巴蕾公司的责任财产缺失,侵害到了作为金巴蕾公司债权人的宏王达厂的财产权益。但对杨美勤而言,其没有缴纳的股东出资是可能给金巴蕾公司债权人造成的最大损失,因金巴蕾公司无法清偿其所欠宏王达厂债务,且未清偿债务金额已超过股东认缴出资额,杨美勤作为金巴蕾公司的股东应以出资金额为限向宏王达厂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如杨美勤无法补足出资的,则诚洲公司总共应承担50万元的赔偿责任,但是,在杨美勤承担赔付责任后,诚洲公司50万元的赔偿金额应相应减少。
三、关于顾忠华、顾增荣的责任问题。顾忠华和顾增荣均非金巴蕾公司的股东,宏王达厂以顾忠华为金巴蕾公司虚假出资的实施者为由要求其承担金巴蕾公司的债务,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而顾忠华以金巴蕾公司名义骗取宏王达厂货物的行为触犯刑律,因此已受到刑事处罚。对于宏王达厂被骗财物损失,(2009)浙嘉刑初字第20号生效刑事判决已判令相关被告人向受害人退赔,宏王达厂又于本案中以此为由要求判决顾忠华承担金巴蕾公司的债务,不予支持。顾忠华、顾增荣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后,尚有部分查封财产未追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4条规定,“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擅自处分已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责任人限期追回财产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且刑事判决中未对顾忠华、顾增荣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过处理,故宏王达厂于本案中要求顾忠华、顾增荣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应予支持。由于未追回的1540件羽绒服中有500件系顾忠华擅自抵给上海琦慧德工贸有限公司,顾增荣未共同参与,顾增荣承担的赔偿数额中应扣除500件羽绒服所对应的款项。顾忠华系金巴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了解被查封财产的价值,宏王达厂称所查封的羽绒服每件96元、毛条每条21.5元、鸭绒每吨17万元,顾忠华对此没有异议,因此,查封时财产的价值可以确认。宏王达厂所主张的非法处置查封财产损失,包括了已追回查封财产的贬值损失,该损失与非法处置行为没有必然联系,宏王达厂主张的损失金额,不予采信。同理,顾忠华和顾增荣也不能按追回财产的评估抵债价格计算未追回查封财产的价值,否则,顾忠华和顾增荣会因其非法行为而获利。故对于无法追回的查封财产,应按羽绒服每件96元、毛条每条21.5元、鸭绒每吨17万元计算损失金额,由顾忠华和顾增荣向宏王达厂赔偿。
综上所述,宏王达厂对金巴蕾公司享有债权,金巴蕾公司丧失清偿能力致宏王达厂债权受损,诚洲公司、杨美勤、顾忠华和顾增荣应向宏王达厂承担债权损失的责任,但由于各自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不完全一样,一般而言,存在着各自的责任顺序问题。顾忠华和顾增荣非法处置的查封财产属于金巴蕾公司所有,顾忠华和顾增荣的行为直接导致金巴蕾公司不能以其所有的被查封的财产清偿债务,顾忠华和顾增荣的责任居先;当包括被查封财产在内的金巴蕾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应由杨美勤等股东在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杨美勤的责任居次;如杨美勤承担责任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诚洲公司应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诚洲公司的责任居后。因宏王达厂所受债权损失超过本案中确定的诚洲公司、杨美勤、顾忠华和顾增荣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总额,故当事人赔偿顺序的先后不影响被告方各自或共同向宏王达厂承担支付赔偿金额,但是,在杨美勤承担后,应减少诚洲公司的给付金额。顾增荣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缺席判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2010年8月31日判决:一、诚洲公司在金巴蕾公司50万元注册资金(股东认缴的出资金额)范围内向宏王达厂承担赔偿责任。二、杨美勤赔偿宏王达厂损失10万元(杨美勤认缴的出资金额)。三、顾忠华赔偿宏王达厂损失497294元。四、顾增荣对上述第三项顾忠华所承担赔偿金额中的44929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宏王达厂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608元,由宏王达厂负担13304元,由诚洲公司负担5000元,由杨美勤负担1404元,由顾忠华负担4900元,顾增荣对顾忠华所负担诉讼费部分的4250元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宏王达厂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对查封财产未追回部分的价值认定为497294元有明显错误,而应当认定为1425580元。1.原查封的财物与追回的财物在质量与规格上有明显差别,不能简单地将原查封的财物与后来追回的财物从数量上相减后以同样的价格进行计算得出未追回部分的价值。如:原查封的貉子毛条是大毛条,平均每条21.50元,而追回的是小毛条,当时的价格一般在每条5元左右;原查封的鸭绒是正品鸭绒,每吨价格17万元,而追回的是混碎性鸭绒,每吨3万元左右,最高也在4万元以下;原查封的羽绒服是正品,而追回的是次品。2.追回财物的价格应当以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认定,因为评估机构是根据当时的实物品种、规格、质量和市场价格所作的科学结论。3.所谓查封后财物价格下跌的辩解没有根据。2007年被查封后的6、7、8三个月,这些物品的市场价格确有回落,但从8月开始,又有上涨,到2008年3月20日评估日时,价格已与查封时相当,不存在贬值的问题。即使价格略有差异,也应以当时用于抵债时的实际价值为依据。4.刑事案件庭审时,顾忠华和顾增荣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辩解,但公诉人当庭反驳认为追回的财物与被非法处置的查封财物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相差很远,应以评估结论为准。二、原判未否定金巴蕾公司法人人格并认为杨美勤不应负连带责任与事实和法律不符。1.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和《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达到法定注册资本是公司设立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股东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原判虽认定金巴蕾公司从成立一开始就因股东出资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责任财产,让金巴蕾公司股东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却披上“合法出资的外衣”,致与金巴蕾公司进行交易的主体处于危险境地,但对不符合公司必备条件无注册资金的金巴蕾公司不否定法人人格,前后互相矛盾。2.(2009)浙嘉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金巴蕾公司系虚报注册资金而成立的空壳公司,顾忠华兄弟等利用公司有限责任大量向外骗货,其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行骗。从后果看,使债权人无法实现民事清偿和刑事追赃的目的。故否定金巴蕾公司法人资格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判未判令杨美勤负无限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其没有参与抽逃出资,没有以金巴蕾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没有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事实是:杨美勤明知自己分文未出资,却在股东会决议和工商变更申请表上签名虚构自己出资10万元的事实,这本身就是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同时,杨美勤将金巴蕾公司副总顾忠华的房产无正当理由过户到自己名下,企图从中获大利,并利用该房产为金巴蕾公司向银行贷款25万元。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杨美勤并非金巴蕾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实际在参与经营,还帮助参与转移不义之财。故杨美勤负连带责任理所当然。4.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三)项等规定精神,对于股东出资不足均规定了由股东互负连带责任,更何况无任何出资,实际上各股东成了一种合伙关系,更应依法互负无限连带责任。综上,请求:认定原查封财产未追回部分数额为1425580元;否定金巴蕾公司的法人人格,杨美勤对金巴蕾公司尚欠宏王达厂的货款及利息负无限连带责任。
上诉人顾增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是侵权纠纷,宏王达厂没有举证证明顾增荣侵犯其财产的事实。宏王达厂起诉的是买卖合同纠纷,但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有买卖合同。诉讼中宏王达厂没有要求变更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擅自变更法律关系没有依据。二、宏王达厂请求判令顾增荣赔偿非法处置被查封财物1208000元没有举证证明。非法处置被查封财物所有权的是金巴蕾公司,不是顾增荣。原审法院判令顾增荣对449294元赔偿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宏王达厂没有诉权,应当驳回起诉。三、宏王达厂起诉所用证据是原审法院的两份判决书,自相矛盾。宏王达厂在2006年曾与金巴蕾公司签订过4份买卖合同,欠宏王达厂货款是事实。宏王达厂先以合同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判决支持后,又以同一事实向公安机关举报是合同诈骗。原审法院又以同一事实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是合同诈骗。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先后作出二份不同性质的判决,根据逻辑推理必有一个判决错误。如果刑事判决是对的,则宏王达厂与金巴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就是错的,应当依法撤销。撤销后非法处置被查封财物罪名就不成立。四、原审法院以尚有部分查封财物未追回为由,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4条为法律依据支持宏王达厂赔偿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查封财物应不应该追回是刑事判决应当解决的问题。处置的是金巴蕾公司的财产,宏王达厂无权向法院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执行中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执行程序中的问题,不是宏王达厂可以起诉的依据和理由。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宏王达厂的起诉。
针对宏王达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顾增荣在法定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辩称:宏王达厂把顾增荣列为被上诉人,与其上诉理由不符。因为宏王达厂没有明确要求顾增荣承担责任,其上诉请求与顾增荣无关。
针对顾增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宏王达厂在法定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辩称:一、宏王达厂将顾增荣作为被告起诉完全合法。顾增荣非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的事实已被一、二审刑事判决所认定,其行为使宏王达厂的债权无法得到执行,其完全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鉴于本案系宏王达厂与金巴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在执行阶段派生出来的案件,故宏王达厂起诉时用了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原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案由并得到宏王达厂的认可是法律所允许的。二、原判认定非法处置查封财物的价值已由顾忠华当庭认可,并非没有证据。顾增荣非法处置查封财物负连带赔偿责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查封财物所有权归属尚未确定,就本案而言,完全属宏王达厂可以依法执行的财物。因此,宏王达厂完全有权起诉。三、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可以同时存在,本案民事判决在前,刑事立案和起诉判决在后。正如刑事判决所述,民事责任不能代替刑事责任。被害人的损失可以通过刑事追赃,也可以通过民事执行得到挽回,两者并不矛盾,而且应是民事优先原则。鉴于本案诈骗的特点是公司无财产可执行,公司主要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又事先转移财产。故宏王达厂只能通过起诉追加被执行人,实现生效判决的实际执行。
被上诉人诚洲公司针对宏王达厂和顾增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法定答辩期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辩称:宏王达厂的上诉请求与一审的诉讼请求以及一审判决诚洲公司承担的责任及理由没有任何关联,故诚洲公司对宏王达厂的上诉请求和事实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不予答辩。顾增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与诚洲公司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没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诚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也向本院提起上诉,但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故诚洲公司在二审中的诉讼地位为被上诉人。
二审期间,宏王达厂提交二份证据:1.嘉兴联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嘉联评〔2008〕第6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证明评估资产的品种、数量和价值,其中23600条系小毛条,鸭绒为混碎绒。2.原审法院(2007)嘉中法执字第14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查封财产用于抵偿金巴蕾公司的债务,而不是抵偿顾增荣与顾忠华非法处置的查封财物。顾增荣和诚洲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认为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2宏王达厂一审时已经提交,证据1系证据2民事裁定拍卖和抵偿的依据,在一审期间已经存在,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2007年1月19日作出的(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查封令载明:对金巴蕾公司位于嘉善商城北五街8-10号仓库内的货物:楼下仓库各式羽绒衫2000件、鸭绒约3吨和楼上仓库各式羽绒衫1580件、各式毛条26600条。2008年1月29日作出的(2007)嘉中法执字第14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对(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查封令查封的现由被执行人转移至“江南乐章”小区5-10车库内各式毛条213捆(100条/捆)共计21300条予以继续查封,同时指令宏王达厂对上述物品自行妥善保管,未经许可不得转让、出售、抵押、处置等;同年2月15日作出的(2007)嘉中法执字第149-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对原查封的现由被执行人转移至嘉善嘉洲阳光花园16幢3号厂库内鸭绒42包、各式羽绒服2120条、小毛条2300条予以继续查封。查封期间,由宏王达厂妥善保管,未经许可不得出售、转让、质押等。同样,对追回物品的规格、质量和价格均未明确。嘉兴联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8年4月9日作出的嘉联评报〔2008〕第6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的鸭绒为混碎绒。2008年6月27日作出的(2007)嘉中法执字第149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查封的金巴蕾公司所有的鸭绒1323.8公斤、小毛条23600条、男女各式羽绒服2040件,作价172000元交付宏王达厂所有。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查封财产未追回部分的价值是多少;杨美勤对金巴蕾公司尚欠宏王达厂的货款和利息应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宏王达厂对顾增荣是否享有诉权。(一)关于查封财产未追回部分的价值。原审法院(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宏王达厂和金巴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宏王达厂的申请,于2007年1月19日查封了金巴蕾公司的财产,对查封财产的数量和价值,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此后,顾忠华和顾增荣擅自将查封的财产进行处理,后仅追回部分查封财产,评估价值为214776元。因公开拍卖未果,原审法院以拍卖保留价172000元抵偿给宏王达厂。本案中,原审法院将原查封物品的数量减去已追回物品的数量,按照宏王达厂和顾忠华在庭审中确认的查封物品的价格,得出查封财产未追回部分的价值为497294元,判令顾忠华和顾增荣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宏王达厂认为追回的物品与原查封的物品的规格和质量均不同,对原查封物品的价值没有异议,但认为追回的部分没有原查封物品的价格高。因此,对未追回部分查封物品的价值认定,应为原查封物品的价值1425580元减去追回部分物品的评估价值214776元得出1210804元,二审庭审中变更为1425580元,因原审法院裁定抵偿的系金巴蕾公司的债务,而非顾增荣和顾忠华非法处置查封财产产生的债务,故应全额计算。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无论是原审法院查封令载明的内容,还是民事裁定书载明的内容,对查封物品以及追回物品的规格、质量和价格均未明确,宏王达厂在查封现场也未要求明确,追回物品由宏王达厂保管的情况下,也未明确。因此,宏王达厂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追回的物品非原查封的金巴蕾公司的财产。另外,顾忠华和顾增荣非法处置被追回的查封财物,本系金巴蕾公司的财产,追回后用于抵偿金巴蕾公司对外债务,理应减轻顾忠华和顾增荣的民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未追回部分的查封物品价值为497294元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予维持。(二)关于杨美勤的民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本案中,成立金巴蕾公司由顾忠华委托诚洲公司办理,签订合同骗取宏王达厂货物由顾忠华和顾伟华共同所为,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系顾增荣和顾忠华共同实施,杨美勤均未参与上述行为,而且宏王达厂也无证据证明杨美勤还存在其他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因此,宏王达厂认为杨美勤应对金巴蕾公司尚欠宏王达厂的货款和利息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三)关于宏王达厂对顾增荣的诉权问题。首先,关于法律关系。宏王达厂起诉案由虽为买卖合同纠纷,但经原审法院释明,确定为侵害债权纠纷,宏王达厂也表示同意。故原审法院变更案由并无不当。其次,关于顾增荣非法处置查封财物的问题。顾增荣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的事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所认定,并被定罪量刑。因此,顾增荣非法处置被查封财物的行为足以认定。顾增荣非法处置查封财物,导致宏王达厂胜诉后,债权不能实现,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顾增荣侵害宏王达厂债权,判令其承担未追回部分查封财产的损失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关于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的关系。(2007)嘉民二初字第17号案件系宏王达厂与金巴蕾公司、顾伟华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判决金巴蕾公司支付货款,保证人顾伟华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而刑事判决认定顾忠华、顾伟华个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金巴蕾公司。因此,两者并不存在矛盾。按照刑事判决认定,顾增荣并未犯合同诈骗罪,其非法处置查封财产侵害他人债权,原审法院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最后,顾忠华、顾增荣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后,尚有部分查封财产未追回,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4条“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擅自处分已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责任人限期追回财产或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考虑到刑事判决中未对顾忠华、顾增荣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过处理,对宏王达厂于本案中要求顾忠华、顾增荣为此承担赔偿责任予以支持正确。债权人是通过刑事追赃还是通过民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利,享有选择权。因此,宏王达厂对顾增荣享有诉权。
综上,上诉人宏王达厂和顾增荣相应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974元,由桐乡市崇福宏王达裘皮制品厂负担10935元,顾增荣负担803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裕 灿
审 判 员 徐 向 红
代理审判员 孙 光 洁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 云 芳
浙XX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杜利法、李永儿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浙XX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杜利法、李永儿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浙06民初400号
原告: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丁天方,系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管理人的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苏苏,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被告:杜利法。
被告:李永儿。
被告:何兴祥。
被告李永儿、何兴祥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桥,浙江中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萍儿。
原告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因与被告杜利法、李永儿、何兴祥、李萍儿追收未缴出资、抽逃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袁小梁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柳雪松、人民陪审员金玲萍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8月2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判决。原告华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宇、俞苏苏,被告李永儿、何兴祥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桥到庭参加庭审,被告杜利法、李萍儿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夏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杜利法向原告返还抽逃出资本金人民币450万元,并支付从抽逃出资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李永儿、何兴祥、李萍儿对前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4年9月11日,浙江绍兴银桥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桥公司)以华夏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绍兴中院)申请对华夏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14年10月16日,绍兴中院作出(2014)浙绍破(预)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受理该破产清算申请,并作出(2014)浙绍破字第2-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担任华夏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经对华夏公司审计,管理人发现华夏公司的股东香港龙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龙康公司)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具体如下:华夏公司于2003年9月9日成立,注册资本美元1180万元,其中香港龙康公司(经查实,香港龙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杜利法妻子的弟弟)认缴注册资本美元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84.75%,杜利法认缴注册资本美元180万元,占注册资本15.25%。根据2009年1月5日董事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华夏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美元518.801281万元,实收资本不变,变更后的注册资本美元661.198719万元,实收资本美元661.198719万元,持股比例为香港龙康公司91.50%、杜利法8.50%。截至2014年10月16日,华夏公司账面实收资本为美元661.198719万元,折合人民币5262.6225万元,其中香港龙康公司出资美元605万元,折合人民币4812.6225万元,占比91.50%,杜利法出资美元56.20万元,折合人民币450万元,占比8.50%。经审计,香港龙康公司涉嫌抽逃注册资金人民币1566.988万元、利用公司原有资金虚假出资人民币2904.645万元,杜利法涉嫌抽逃注册资金人民币450万元,合计人民币4921.633万元,注册资本实际到位人民币340.9895万元。各期注册资本到位情况如下:
1.设立出资第1期
设立出资第1期由香港龙康公司出资美元160万元,折合为人民币1324.19万元,出资日期为2003年11月14日,业经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宏会验字[2003]第859号验资报告。验资之后,华夏公司于2003年11月25日通过银行向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转账1200万元,截至2014年10月16日尚未归还。经查实,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华夏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利法的妹夫(2014年8月18日变更为杜利法的妹妹)。香港龙康公司涉嫌抽逃第1期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
2.设立出资第2期
设立出资第2期由香港龙康公司出资美元140万元,折合为人民币1156.988万元,出资日期为2004年6月17日,业经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宏会验字[2004]第411号验资报告。出资之前,华夏公司于2004年6月15日通过银行向李萍儿转账450万元、向李碧祥转账500万元。验资之后,华夏公司于2004年6月18日通过银行向李碧祥转账226万元。经查实,李萍儿为华夏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利法的妻子,李碧祥为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出纳。香港龙康公司涉嫌利用公司资金虚假出资人民币950万元,涉嫌抽逃注册资本人民币206.988万元,第2期注册资本1156.88万元未实际到位。
3.设立出资第3期
设立出资第3期由杜利法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出资日期为2006年6月12日,业经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宏会验字[2006]第467号验资报告。出资之前,华夏公司于2006年6月9日银行转账350万元给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验资之后,华夏公司于2006年6月13日银行转账100万元给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合计450万元。杜利法涉嫌利用公司资金虚假出资人民币350万元,涉嫌抽逃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第3期注册资本450万元未实际到位。
4.设立出资第4期
设立出资第4期出资由香港龙康公司出资美元250万元,折合人民币1954.645万元,出资日期分别为2006年11月16日出资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92.64万元),11月27日出资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91.265万元),12月18日出资8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24.432万元),12月22日出资7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6.308万元),业经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宏会验字[2006]第838号验资报告。出资之前,华夏公司于2006年11月14日通过银行向李萍儿转账220万元,向郎小英转账200万元,合计420万元;于2006年11月21日通过银行向郎小英转账200万元,于2006年11月22日通过银行向李萍儿转账200万元,合计400万元;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银行向李萍儿转账400万元,向郎小英转账240万元,合计640万元;于2006年12月19日通过银行向李萍儿转账300万元,向郎小英转账260万元,合计560万元。香港龙康公司涉嫌利用公司资金虚假出资人民币1954.645万元,第4期注册资本1954.645万元未实际到位。
5.设立出资第5期
设立出资第5期出资由香港龙康公司出资美元55万元,折合人民币376.7995万元,出资日期为2008年12月8日,业经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宏会验字[2008]第460号。验资之后,华夏公司于2008年12月18日,以现金方式向香港龙康公司支付160万元,香港龙康公司出具收据。香港龙康公司涉嫌抽逃注册资本人民币160万元。
6.账面债权反映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述涉嫌抽资、虚假出资在华夏公司账面反映为其他应收款——对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应收1650万元、对李萍儿应收1570万元、对李碧祥应收726万元、对郎小英应收700万元、对香港龙康公司应收160万元、对浙江绍兴宏发利真空镀铝膜有限公司应收200万元,合计5006万元。
自2014年2月起,华夏纺织通过现金归还、以自有资金支付给关联方后又转账归还等形式,减少其他应收款——李萍儿1570万元、李碧祥726万元、郎小英700万元,合计2996万元。同时,增加其他应收款—浙江绍兴宏发利真空镀铝膜有限公司2359.23万元,现金购买原材料、备品备件等支出636.77万元;购买的原材料、备品备件等又以20%左右的折扣低价出售给浙江绍兴宏发利真空镀铝膜有限公司,未收到销售款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或者返还抽逃的出资本息,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或者违反出资义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管理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公司的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并将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二、三、四作为协助杜利法抽逃及虚假出资的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以及董事,应承担连带责任。
杜利法未到庭参加诉讼,其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自己2003年10月到袍江工业区投资因需外商投资才能入户,后经人介绍拿了李永儿的身份证办了香港龙康公司,华夏公司因担保出现资金问题,后被银桥公司申请破产。李永儿是自己的大舅子、香港龙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开办公司时拿了他的身份证,开户是介绍人办理的,李永儿不在公司上班,没有拿过公司工资,未参加公司会议。何兴祥2006年7月进入公司,当时职务是采购员,2008年后因公司贷款担保需要三个董事签字让其担任董事,但其实际工资是中层员工工资。
李永儿、何兴祥共同辩称,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杜利法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原告只是提供了管理人制作的一份审计报告,其他相关证据没有,证据不足。据了解,华夏公司2003年成立的时候,袍江管委会招商引资必须要外商投资这种模式,均是由管委会的相关人员介绍认识,只要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去香港注册一家公司就可以了,作为杜利法或袍江其他企业都不清楚外资、外商具体形式,当时都有这种情况,公司相关人员不清楚具体操作。即使杜利法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李永儿也不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永儿只是挂名的副董事长,在公司从未上过一天班,也没有工资收入,开会从未参加,当时因为亲戚关系提供了身份证,现在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与公司法规定的权利义务一致相违背,董事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李永儿作为形式上的副董事长,也没有义务监督股东出资,李永儿协助杜利法抽逃出资缺乏证据,原告要求李永儿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何兴祥是2006年7月进入公司作为采购废塑料的人员,2009年因贷款需要才担任董事,但何兴祥并不是高管,工资也是采购废塑料员的工资,没有权利参加会议,而原告认为杜利法是2006年6月进行抽逃出资,因此何兴祥也不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李萍儿未作答辩。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夏公司破产受理日报表的审计报告一份,证明经审计确认被告杜利法、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2.企业登记基本情况一份,证明被告二、三、四在华夏公司担任董事。
李永儿、何兴祥质证认为,对于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审计报告是管理人出具的,实际应该由第三方出具,从内容上也无法看出杜利法抽逃出资450万元,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企业登记基本情况真实性没有意见,三人确实是董事,但实际上都是由杜利法在操作,李永儿、何兴祥只是挂名的,登记表上也无法看出李永儿、何兴祥有监督股东出资的情况,也无法反映出有协助杜利法抽逃的行为。
被告李永儿、何兴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3.华夏公司2005年、2006年到2014年的部分工资单,工资单上全部没有李永儿的名字;4.华夏公司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纪要及签字的材料,也都没有李永儿的名字,何兴祥只是普通员工,不是公司高管;5.李其儿的书证,证明李永儿没有上班、没有参加会议及何兴祥为什么作为董事的说明。
华夏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3、4三性均无异议,对李永儿不在公司任职,何兴祥作为一般采购员工予以认可,但李永儿也是香港龙康公司注册的时的实际经办人及法定代表人,且李永儿与杜利法关系密切,李永儿对这件事情应该是明知并且参与的。对于证据5,证人必须到庭,不符合证人证言形式,但原告确认这个签字是证人本人签的,证明的事实内容也予认可。
被告李永儿、何兴祥向本院申请证人杜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并形成证人证言一份(证据6),杜某称,自己是2005年进入华夏公司担任会计,李永儿虽然是董事,但其没领工资,没参加公司董事会或中层会议,何兴祥只是公司普通业务员,是因为公司一名董事到其他单位缺少董事在2009年、2010年加进来的,其只是名义董事,没有董事的待遇和权利。管理人制作的审计报告自己看过,比较客观。华夏公司、李永儿、何兴祥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杜利法、李萍儿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证据的质证权利。原告与到庭被告对证据2、3、4、6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杜利法未提出异议,且系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形成的报告,被告李永儿、何兴祥虽提出异议,但也明确表示不申请审计,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以确认。证据5中的证人未到庭,但原告认可证人签名及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与其他证据可以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查明:华夏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9日,注册资本美元1180万元,后减资为注册资本661.1987万美元,股东为香港龙康公司、杜利法,杜利法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永儿为副董事长,何兴祥、李萍儿为董事。何兴祥2006年7月进入华夏公司工作,2009年开始担任董事。2014年9月11日,银桥公司以华夏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华夏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14年10月16日,本院作出(2014)浙绍破(预)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受理该破产清算申请,并作出(2014)浙绍破字第2-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合管理人)担任华夏公司管理人。后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华夏公司进行破产审计形成审计报告,具体内容为:华夏公司于2003年9月9日成立,注册资本美元1180万元,后变更注册资本为美元661.198719万元,实收资本美元661.198719万元,截至2014年10月16日,华夏公司账面实收资本为美元661.198719万元,折合人民币5262.6225万元,其中香港龙康公司出资美元605万元,折合人民币4812.6225万元,占比91.50%,杜利法出资美元56.20万元,折合人民币450万元,占比8.50%。经审计,杜利法涉嫌抽逃注册资金人民币450万元,具体为设立出资第3期由杜利法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出资日期为2006年6月12日,业经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宏会验字[2006]第467号验资报告。出资之前,华夏公司于2006年6月9日银行转账350万元给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验资之后,华夏公司于2006年6月13日银行转账100万元给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合计450万元。杜利法涉嫌利用公司资金虚假出资人民币350万元,涉嫌抽逃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第3期注册资本450万元未实际到位。截至2013年12月31日,相关涉嫌抽资、虚假出资在华夏公司账面反映为其他应收款,其中对李萍儿应收157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管理人以公司股东及高管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为由提起的破产衍生诉讼,应为追收未缴出资、抽逃出资纠纷案件。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杜利法是否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情形;二、如果杜利法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情形,李永儿、何兴祥、李萍儿作为董事,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华夏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关于华夏公司破产受理日报表的审计报告一份,虽然该审计报告并非第三方制作,且李永儿、何兴祥对审计报告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杜利法本人并未提出异议,且该审计报告系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形成,李永儿、何兴祥虽提出异议,但也明确表示不申请审计,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予确认,可以认定杜利法通过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虚假出资350万元,验资之后,杜利法又通过绍兴县联华纺织有限公司抽逃注册资本100万元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管理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公司的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并将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董事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承担相应责任的前提是其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协助抽逃出资,本案中,李永儿虽然是华夏公司副董事长,但其并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未在公司领取报酬,何兴祥在杜利法出资时并非公司董事,华夏公司要求李永儿、何兴祥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李萍儿系公司董事、杜利法妻子,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华夏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股东涉嫌抽资、虚假出资在公司账面反映为其他应收款中,华夏公司对李萍儿应收款为1570万元,李萍儿的行为构成协助抽逃出资,华夏公司要求李萍儿对杜利法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杜利法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并赔偿上述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损失(其中350万元从2006年6月9日开始计算、100万元从2006年6月13日开始计算,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被告李萍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2800元,由被告杜利法、李萍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袁小梁
审 判 员 柳雪松
人民陪审员 金玲萍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冯 莹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等诉孙成杰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浙丽商初字第32号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诉讼代表人:王成良。
委托代理人:林三忠。
被告孙成杰,现羁押于浙江省第三监狱)。
被告李静。
被告朱建国。
被告姚云芳。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叶飞。
被告蔡俊杰。
被告郭爱芬。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董其博。
被告崔婷。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孙成杰、李静、朱建国、姚云芳、蔡俊杰、郭爱芬、崔婷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林三忠,被告孙成杰,被告朱建国、姚云芳的委托代理人叶飞,被告蔡俊杰、郭爱芬的委托代理人董其博,被告崔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起诉称:案外人温州市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经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了(2013)丽松商初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10日前支付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25332989.53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调解书确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均未自动履行。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就其所享有的债权与原告达成债权转让协议。2013年7月17日,由于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松阳法院作出裁定终结了案件执行程序。
经查,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系被告孙成杰、李静设立的空壳公司。2010年6月左右,孙成杰、李静欲成立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缺少注册资金,遂联系被告朱建国、蔡俊杰、崔婷,由被告朱建国、蔡俊杰、崔婷于2010年6月29日将5000万元分别转入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名下用于成立该公司.该公司登记手续完成后于2010年7月1日、2日分两次将5000万元抽走。
综上所述,被告孙成杰、李静系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被告蔡俊杰、朱建国、崔婷明知被告孙成杰、李静虚假注资成立公司仍予垫资帮助,各被告的行为直接导致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减少,造成原告合法债权得不到实现应承担相应责任。而被告姚云芳、郭爱芬分别为朱建国、蔡俊杰的妻子,也应承担民事责任。为此,要求判令各被告在5000万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原欠货款本金25332989.53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
被告孙成杰口头答辩称:原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欠付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属实,但对债权转让的情况不清楚。原告所称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5000万注册资金被抽走也是事实。
被告李静书面答辩称:一、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及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答辩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已经人民法院判决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被答辩人提起本案的民事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公司法、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对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等取得公司登记的,仅规定了责令整改、处以罚款、撤销公司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因此答辩人不存在连带偿还责任,而且答辩人的诉请也不符合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赔偿规定。三、被答辩人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应承担抽逃出资的连带偿还责任。被答辩人诉状所称的事实很明确,2010年6月左右,孙成杰、李静欲成立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缺资金,由朱建国等人出资成立代办注册。朱建国等人将5000万元转入代办公司注册后将该5000万元抽走。其出资款始终不是由孙成杰、李静所有,因此答辩人没有将出资抽走。四、答辩人李静对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注入及注册完成后被抽走并不知情,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孙成杰。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依据不足,要求驳回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朱建国、姚云芳口头答辩称:要求法院查实原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欠付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即使该欠付的货款是真实合法存在的,原告要求朱建国承担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而原告要求姚云芳承担法律责任则更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被告蔡俊杰、郭爱芬口头答辩称:蔡俊杰只是联系借款人,并不存在侵犯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主观过错。原告起诉所依据的法律依据也即最高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十五条规定,已被最高院修改司法解释的决定删除,因此原告起诉蔡俊杰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另外原告起诉的基础是其与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要求对原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所享有的债权进行审查核实。对于本案所涉的任何事情,郭爱芬均不知情,原告针对郭爱芬的起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要求驳回原告对蔡俊杰、郭爱芬的诉讼请求。
被告崔婷口头答辩称:我是为蔡俊杰、朱建国打工的,仅仅是监督资金的安全,原告起诉我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诉讼代表人身份证明各一份;2、被告孙成杰、李静、朱建国、姚云芳、蔡俊杰、郭爱芬、崔婷身份信息材料各一份,待证原、被告的身份主体情况。第二组证据:(2013)丽松商初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待证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欠付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25332989.53元及逾期利息。第三组证据: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变更执行申请人的申请及松阳县人民法院(2013)丽松执民字第497-1号、第497-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待证原告受让温州信合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债权后债务人未清偿该债务。第四组证据:(2012)丽松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书,待证被告孙成杰、李静因虚报注册资本被追究刑事责任;朱建国、蔡俊杰垫资5000万元用于注册公司验资,被告崔婷实际办理虚假出资业务并监督注册资金的抽回。被告孙成杰经质证认为,第一、二、四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债权转让的事实不清楚。被告朱建国、姚云芳经质证认为,第一、四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调解书涉及货款的真实、合法性要求法院进行查实;第三组证据中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蔡俊杰、郭爱芬经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二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所涉货款的真实性存有质疑;第四组证据并不能证明蔡俊杰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被告崔婷经质证认为,第一、四组证据无异议;第二、三组证据并不清楚。本院认为,原告方所提供的第一、四组证据,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系生效法律文书,被告朱建国等人虽存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原告所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等与业已生效的民事裁定相互印证,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也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除查明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称的事实外,另查明:被告孙成杰系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院认为,被告孙成杰作为实际控制人、被告李静作为股东在设立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的过程中利用虚假购销合同抽逃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的事实,已被发生法律效力的松阳县人民法院(2012)丽松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书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20日发布)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作为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诉请被告孙成杰、李静在抽逃出资数额范围内对其未受清偿部分的债务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朱建国、蔡俊杰及崔婷分别为案涉5000万元款项的出借人或款项往来具体经办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条“删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以及第十三条“本决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股东出资相关纠纷案件,适用本决定;本决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决定。”的规定,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请前述三被告承担因被告孙成杰、李静抽逃注册资金而产生的相应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基于前述理由,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要求被告姚云芳、郭爱芬承担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讼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李静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李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放弃对原告方所举证据放弃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20日发布)第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静应当在其对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抽逃出资5000万元金额的范围内,对松阳瑞祥贸易有限公司欠付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债务25332989.53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被告孙成杰对前述被告李静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9270元,由被告孙成杰、李静负担;诉讼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900元,由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允平
审 判 员 聂伟杰
代理审判员 陈俊明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郑丽珍